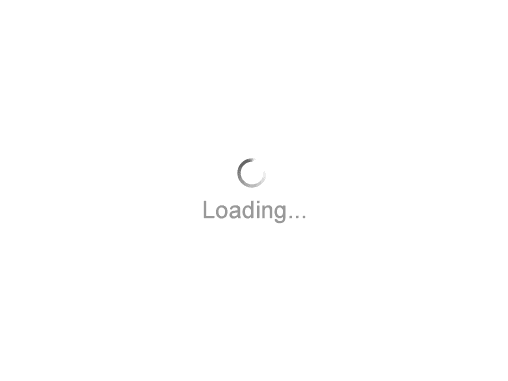啓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
出版时间:2008/11/19 出版社: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Horkheimer, Max 译者:林宏濤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著作,
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文本,
繁體中文完整版首度問世,華語世界引頸期待已久。
馬克斯‧霍克海默與提奧多‧阿多諾所合著《啟蒙的辯證》是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文本,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哲學的經典著作。兩位學者的哲學批判、與法西斯主義的爭論,以及流亡美國時期的研究成果,在此融合成為現代大眾文化的理論。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以最縝密、銳利的思考,為世人闡述了科技與社會進步的反面:「啟蒙」以理性統治,並使自然屈服於人類的各種需求,對此有必要予以啟蒙。
「我們沒有任何懷疑……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但是我們也相信清楚看到了,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這麼註定了。」
--馬克斯‧霍克海默&提奧多‧阿多諾
作者简介
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社會哲學家,出生於德國一猶太家庭,1922年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25年成為該大學教授,1930年升正教授,同時參與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院」(Ins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建立並擔任院長一職。1932~1939年間,創辦《社會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納粹時期,於1933年流亡至美國,與阿多諾、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人在紐約繼續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二次大戰後於1949年返德,五○、六○年代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並重建「社會研究院」。獲頒法蘭克福「榮譽市民」。1973年卒於紐倫堡。其著作經由學生與繼任者施密特(Alfred Schmidt)等人整理後出版為全集。
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作曲家。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父親為酒商,是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母親為歌唱家、天主教徒。原姓Wiesengrund,納粹時期,以母親本姓的Adorno更改為他的姓氏,將原姓縮寫為 W,而成為Theodor W. Adorno。有一位阿姨是鋼琴家,從小接受音樂方面的薰陶。1921年起,於法蘭克福大學攻讀哲學、音樂學、心理學與社會學。1924,即取得博士學位。
在這段求學時期,結識了重要的學術夥伴:霍克海姆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3年前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之後流亡美國,返德後,重回法蘭克福大學教學與研究,1958年主持「社會研究院」。有「社會哲學家」的稱號,便是著重於其哲學思想中社會批判的面向,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學術地位顯赫。
在六○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曾引發一些爭議,1969年被迫停課,並以證人的身分出席法庭。之後,與妻子前往瑞士山區避暑,因心臟不適送醫,心肌梗塞過世。2003年,為紀念阿多諾100冥誕,法蘭克福大學附近的廣場更名為「阿多諾廣場」,並有哲學家紀念碑,其造形為一間玻璃屋,內陳設書桌與椅子,桌上還有一節拍器。
重要著作有:《啟蒙的辯證》、《新音樂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又譯「小倫理學」,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1951)、《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ktik,1966)、《美學理論》(Ästhetische Theorie,1970)。
书籍目录
◎〈導讀〉
◎新版(一九六九年)序言
◎前言
◎啟蒙的概念
Begriff der Aufklärung
◎附論一:奧德修斯,或神話與啟蒙
Exkurs 1: Odysseus oder Mythos und Aufklärung
◎附論二:茱麗葉:或啟蒙與道德
Exkurs II: Juliette oder Aufklaerung und Moral
◎文化工業:作為群眾欺騙的啟蒙
Kulturindustrie. Aufklaerung als Massenbetrug
◎反閃族主義的元素:啟蒙的各種限制
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劄記和初稿Aufzeichnungen und Entwuerfe
‧駁博學多聞
‧兩個世界
‧理念蛻變為宰制
‧鬼神理論
‧無論如何
‧動物心理學
‧給伏爾泰
‧分類
‧雪崩
‧因為溝通而造成的隔離
‧論歷史哲學的批判
‧人性的紀念碑
‧從一個犯罪理論的立場
‧進步的代價
‧空虛的恐懼
‧對身體的興趣
‧大眾社會
‧矛盾
‧註定如此
‧哲學和分工
‧思考
‧人與動物
‧宣傳
‧論愚昧的起源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50条)
- 由于要在论文的前言部分论证学术“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性,于是想起了这本陈年古董。这是我十年前读到的第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作品。后来出了新版,阿多尔诺部分是曹卫东翻译的,虽然没读过这个版本,但看到有人说与原文对照的话能看出翻译得不好,我不懂德文,无从判断。我看的这个版本也是从德文原著译出的,但多用短句翻译(译者你辛苦了),所以没有太大的阅读障碍。我是从这本书以及后来读到的一些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开始(包括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文化工业和文化复制理论、弗洛姆的社会文化批判与精神分析理论),建立起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批判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一定要给五星。
这本书当年给我带来的最大的震撼是,”启蒙“不是一种绝对价值,而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康德时代的“启蒙理性”是理想化和圣洁的,然而”启蒙“概念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有可能变成灾难。”意识形态“在当代的发展证明,“启蒙”最终变成了“神话”,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启蒙“的神话当中,人把”天赋人权“和”天赋人智“混为一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明智“的,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基于”自由意志“的,每个人先天就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种盲目性让人丧失了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人失去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启蒙所形成的这种盲目性滋生了反犹主义:犹太民族由于长期的精神自律、以及在教育方面的发达,普遍具有优雅、有教养的特质,使得这个民族在欧洲社会中、尤其是在金融和科技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启蒙“所催生的那种极端”平等“观使得欧洲人产生了要把犹太人从”王座“上拉下来、碾碎在尘埃里的那种”激情“。而这种激情,基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攻击、敌对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或者说是嫉妒)由来已久,但现代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才是前所未有的,比欧洲的野蛮时代更加野蛮。
启蒙的另一个后果是,催生了文化工业中的”伪启蒙“。文化工业把”思想平等“偷换成了”思想一模一样”,即“同一化”。这样就能够让大众方便地消费从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文化产品。启蒙制造出了千人一面的“大众”——需要说的是,这里的“大众”概念是特指文化工业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指“普通人民群众”。所以有人如果使用“大众”这个概念的话,需要谨慎一点。
启蒙不是极权主义者利用和发动群众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就是变成资本家用以开动消费文化机器、疯狂敛财的阴谋。但之所以对启蒙进行这样的”辩证“和”批判“,对启蒙的历史进行这样深刻的挖掘和反思,并不是为了诋毁甚至放弃启蒙,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真正的启蒙精神。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一个世纪前的五四文学和文化就建立在启蒙的基础上,这本来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现代传统,但在今天却是一个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害的传统。一切都源于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的扭曲认识。今天的人并非不谈论”启蒙“,但一种肤浅的启蒙态度让每个人的”无知“都变得理所当然,让基于”启蒙“的”自我“却变成了肤浅和狂妄的”自恋“。1980年代的”新启蒙“,就是这样给启蒙重重地抹了黑,使那一代知识分子丧失了进入历史、呈现真理的使命感,也丧失了对启蒙的信心。
今天重提”启蒙“的时候,别忘了后面一定要有三个字:“辩证法”。辨证和批判思维对个人而言,标志着思想的成熟。对一个社会而言,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人具有真正的辩证和批判思考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文明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的潜力到底如何。
- 阿多诺的启蒙或启蒙批判
[摘 要] 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企图早已实现了。如果启蒙完成以前的世界在启蒙的推动者眼里是草率和嬗变的话,那么他们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阻止这种草率和嬗变继续下去。启蒙开始前,世界的神话幻想没有连贯性,也不具有让它长期保持和谐一致的特性。个体的幻想更是不可甄别和量化的,似乎只有确立起超越于个体的体系,让后者带有力量,才能帮助那些远离启蒙的人离开草率和嬗变的世界。作为目的性的这一点看来达到了。但被告知已完成完美启蒙的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二十世纪以降却屡遭劫难:欧战、二战、战后的虚妄、文化消费的不安等等。对现实问题的反思矛头最终又指回了启蒙运动。回顾整个启蒙过程,起初被称作幻想和其它类似的东西,是如何被启蒙运动嫌弃,而后脱离每个个体的;或者说启蒙对神话的祛除和挤占是伪命题,都成为眼下的问题所在。阿多诺批判启蒙的出发点更加深远,他试图探究启蒙和它想祛除的神话的渊缘。
[关键词] 阿多诺 启蒙批判 神话 反犹主义 工业社会
一
启蒙运动排挤了神话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理性与知识垂青。阿多诺套用启蒙主义者的话说,这是因为理性和知识能够祛除神话,以便让每个个体摆脱掉对神话时代回忆的恐惧,不必被幽魅、神怪捆绑住独立自主的人格。 最终的结论是:被启蒙摧毁的神话,是启蒙自身的产物。 阿多诺认为古代西方社会不全是神话元素,如同启蒙时代也不是没有神话元素一样。 启蒙的理性宣教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反倒能把神话社会解释为一个更好、更合理的社会约束体,靠的是“人神同一论”的普遍方法论。 这样的作用显而易见,自然物和被人们认为的超自然物据此依托人的形象展现了出来。几乎每个古文明神话里都有太阳的人形神。凯尔特神话中的艾索伦(Ethlenn)是太阳神,他有能力控制太阳的显没,同时他又是光明的象征,成了与黑暗和痛苦相对的隐喻,这类似于阿波罗。在古代中国,太阳是“多子多福”的生育结果,曦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是神话时代已经有了那样一种“启蒙”;或者说是启蒙把神话时代发现并展现了出来,是启蒙的“私生子”。这二者看似有不可言说的重合,但这种重合的混乱又被另外的分析掩盖。
我们借用阿多诺的理论再来看这些古老神话、史诗中太阳神的例子。首先,谈论古代中国的“太阳之母”曦和时,还要谈论十个太阳的结局。因为这在后来中国的朴素辩证法和父系制度那里已经显得不够恰当,于是有了另一位有能力破坏自然客体,即射落太阳的后羿。经验世界告知的是一个太阳,也告知了一个太阳的光热最为恰当,它养护苍生且不至于灼伤和杀死苍生。那么,之前十个太阳的子虚乌有就可疑了。编织一个太阳的目的是让其合理性否决十个太阳的不合理,能够生育十个太阳的曦和随即被划入危险的名目。“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 ,庶民百姓不再是单个出现,而是“万民皆喜”。群体性的名词取消了“万民”中单独一位或若干位的性别,让个体不再重要。“名不见经传”的好处是否定了个体的特殊性,赋予意识形态主体性,让它代言个体,也裁判了自己的合理合法。
尽管太阳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许多古代文明都不愿意将它看得和草木一样普通;认识到太阳属于自然界这一点的人,大多具备一定的天相观测经历,也都不情愿把它完全和神脱开关联。古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苏里耶的诞生与俗世无牵挂,这初看倒和上古太阳与人类经验世界的距离相近,可苏里耶又被叙述成“梵”的一部分。这不仅成了脱胎于印度教的圭臬,而且提到苏里耶时,还将提到他最出色的儿子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更成为印度等级制度的解释下沟通宗教与俗世的代言人。代言和裁判的形式很多,但凡有个体发出质疑之声,都会受到惩罚。惩罚的形式虽多种多样,但都逃不出总体性正义的迷宫。它成为禁忌,成为在个体与群体间若即若离的被称之为曼纳(Mana)的东西。随之成为禁忌的就成了触犯禁忌的个体,它被群体的排他意志排除在外。 但由于群体和它的规则不仅在惩罚触犯禁忌者时奏效,也提供生存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中包括食物的获取、和敌人格斗、甚至包括避免犯下触犯这极大的罪的恐吓,那么那个时代的个体就很难冒进地选择独立自主了。甚至还有神话时代的巫术剑指背叛者,在凉山彝族部落中,叛逃部落的人的衣服将被收集在一起,由巫师敲打,旨在让叛逃者迷路。 据此不难看出,那个超离出主体建立起的客体是一切是非善恶的意志来源。吊诡的是,它还隐秘地把自己伪装成个体的想法,让后者毫无分辨的能力。整饬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平衡问题带来宗教的发展, 但正因如此,许多不能抹去的因素让人们在启蒙的道路上背向地越走越远,这在东西方都不少见。
所以,神话带来了盲从和服从,这一直接原因和诸多例子鼓励着启蒙运动向前发展。但阿多诺以一个欧洲人的口吻讲述了奥德修斯神话,他经典的讲述质疑了启蒙运动坚持不懈做下去就能彻底成功的可能性。奥德修斯经过海妖岛屿时,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着他和他的水手们。奥德修斯心生一计,命令水手将他捆绑起来,哪怕海妖释放再大的引诱也不能动弹。至于水手们,奥德修斯用蜡灌注进他们的耳朵里,使其听不到海妖的歌声,以便专心驾驶。 阿多诺认为,荷马史诗里的神话其实也是反神话,它具备反神话的性质和启蒙的痕迹。甚至此后没有其他任何作品有次能力表现神话和启蒙之间模棱两可的关联。
在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里,奥德修斯是个牺牲品。奥德修斯的自缚有多层意义,不妨这样来分析。首先,他捆绑自身的目的在于免于受到海妖诱惑的歌声的干扰,进而让自己的队伍前进。他决定把自己捆绑起来,作为类似于巫师施展巫术的祭品。这种献祭在启蒙者看来是荒谬的,因为他取消了受仪式影响的个体的主体性。其次,他的另一层内涵和启蒙者的方向又惊人地吻合。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水手们,但让自己幸免于此,取而代之的是用另外的肉体折磨虐待自己。水手们因为暂时的失聪豁免于聆听到歌声但又不得不去克服的矛盾心理的痛苦,但奥德修斯本人却无法因此豁免。他在众人面前展现出问道者的形象,从身边的英雄升华为神圣的象征。这样做还有更长远的好处。在与海妖的斗争中,奥德修斯变得与众不同。他不仅让自己的权力带上了神性,笼罩在高于甲板的一处更接近太阳光辉的地方,而且藉此水手们组成另一集团,成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辛苦地驾驶着船只的水手。这与早期的神话社会已然不同,奥德修斯象征着的权力阶层,无论它是世俗权力还是非世俗的权力,抑或二者的巧妙结合,都已经和非权力阶层脱节了。 为了掩饰这种脱节,奥德修斯设置了两个观看的视角,以勾连住他和他的水手。其一是他们共同面对着同样的敌人,不会有人对海妖塞壬的诱惑持否决态度,也不会有人质疑违反禁忌将受到的惩罚的强度;其二则是奥德修斯设下了类似祭坛似的临场,水手们围绕着的奥德修斯就像祭坛上的祭物,奥德修斯此时还充当了巫师的角色。这又是启蒙者看起来荒谬的了,但有一点启蒙者并未察觉。
奥德修斯牺牲了他自己,就像后来新教伦理传达的那样。后者要解放幻想中虚无缥缈的人的思维,却又被投入另一种可以被认定为束缚的理性关系中。这样,启蒙产生出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的对立面就是他所反对的东西的一部分。在奥德修斯的故事里,水手们因听不见水妖塞壬的呼喊,得以保全,并长期保全下去。这已经是对恒常性的追求。在故事开始之前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延续性、重复性、恒常性。但到了这里,在海妖、奥德修斯和水手的三角形结构中,水手找到了延续、重复、恒常。这种避难的代价是每个水手个体的表达就被抹平了,或者说已经有了水手们,水手不再重要。在启蒙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一些相似性便被设定得清清楚楚,不免让后人心生疑虑。其一,和与启蒙运动相伴不衰的工具理性被以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交换的原则成为原则的母本。据此,个体事物在普遍交换中被归之为与另外的事物抽象地等值。 其二,启蒙运动是带有无意识欺诈色彩的祭祀活动。启蒙和神话的合理仅仅一念之差,否定神话的合理性恰恰就是一种对其合理性过程的建立,又翻版而再现了。像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牺牲了,也就牺牲了自然神。就是用这样取消快乐的方法获得恒常的快乐而免于责罚:奥德修斯欺骗了水手们,尽管他们也获得了恒常的快乐,却在诱惑面前被灌蜡,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般的权力控制。而且牺牲自身越文明,就越会释放压制的力量。权力实体从这种社会关系中看到了不真实的地方,和它相关的启蒙与现实就更难融合在一起了。
二
随后的启蒙创造了另一种被概念控制的世界,和启蒙所反对的东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概念性的思维成为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概念也带有了极权色彩。概念的极权体现在它会将每个个体的特质过滤掉,使它们成为被排挤的“异质性碎片”。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中,收集这些异质性碎片并感受到它们的力量,否定全部的关于同一性的哲学即成为他的重要批判。
尽管不是启蒙的本意,但概念试图抑制主体差异,以此创造出主体性的做法在阿多诺看来是极不充分的。最早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正是建立在人开始区分“主体”这个名词背后的歧义,它的所指是含糊不清的。“主体”既可以指向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也可以指向每一个特殊个体的一般意识。 援引阿多诺和卢卡奇争论的一个例子来看。卢卡奇接受并发扬了黑格尔的集体的超主体概念,这个概念在他那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 阿多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个体在作为主体性的意义上,都保有卢卡奇甚至本雅明否定了的重要方式。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谈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异在卢卡奇和早期霍克海默论述主体性和超主体概念时荡然无存。 简言之,因为在意识形态和现实面前,此时谈论个体差异的完全根除并建立理论是不恰当的。
阿多诺把使用“主体”和“客体”等词汇来论证哲学问题看作是“历史的沉淀和传承”,像接力棒一样自然而然地传到了当下这里。概念是“下定义”的媒介,只有借助它,启蒙才能建立起主体和客体的联系,进而让这种联系帮助主体把握客体。 但是,在主体的所指含混不清时,客体是什么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结果造成了无论客体是什么,哪怕是把其他的主体当作客体,都成了可行的了。于是每个个体相互作用,并被带入其中产生异化。主体在生产关系中可以“互换角色”了,主体也将承受来自过往对待自然客体的极权统治。超主体的概念世界以统治者的姿态实现自身,每个人都在其中不能自拔。阿多诺在此坚定地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他一面驳斥庸俗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改良者,驳斥他们的改良行为重复了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客体的统治;一面断言启蒙带来的这个长远问题,延伸到人类劳动,且借助资本主义交换原则和生产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与自然界的不平等、社会内部阶级的不平等。 对此越是讳莫如深,就越会像需要资本家的布施和基督徒的同情怜悯那样,去掩盖启蒙极权带来的不平等。
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不公允之所以会受到阿多诺的强烈反对,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界定的前提具有不可靠的地方,从前提探求事物的本质是危险的。如果给事物下定义的人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利用前人或自己小心界定的前提去论证主体和客体,也必然探求不到事物的本质。下定义变成了自圆其说,并且这样的自圆其说是必定无法和本质无缝契合的,本质甚至会趁机从缝隙间悄悄溜走。那么,从值得商榷的前提出发确定的概念也就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说,通过这些概念获得的本质亦不是本质。概念本身想要反抗和对立与自身不对等的世界,却成为这个世界的内侧要素。这样,在概念反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中,本来就有缺陷的概念又会影响世界,影响人对世界的表达。有一个已建成的当下世界被它影响,就成了有缺陷的了。本来想寻求超越当下世界的批判力量却被这个世界稀释了,在阿多诺看来这个问题过去没有解决,现在依然没有解决。
诚然,每个个体都包括具有普遍内涵的主体概念,但那些普遍内涵覆盖不到的角落更加值得注意。可事实却是,随着启蒙运动达到高潮且看似行将胜利之时,总体性概念针对个体阐释的差异性消除了,现实世界个体间的差异性却还在那里。以阿多诺在音乐上的批判为例,阿多诺不认可成体系的音乐的方法论。首先,音乐通过听觉为人感知,人感知到的音乐和依靠音乐知识习得的音乐几乎不可能相吻合。尽管二者都脱胎于当下世界,但这也正是造成人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分裂和困惑的根源。体系性的音乐能够表现这个音乐体系建立者想表达的音乐真理性,但这种真理性是很有限的,也是难于与每一个经验音乐的个体完全配合得上。另一方面,音乐经验对于每个经验音乐的人而言又是极其抽象的,哪怕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本质的冲击,也几乎不能见诸笔端,更不要说把音乐本质体系化了。 真正探寻音乐本质的方法是从音乐内在发展倾向上去理解,否则音乐体系的力量越是强大,就制造了个体感到现实世界的混乱,最终越接近沉沦其中而忘记反思的可怕终点。阿多诺一直敬仰勋伯格等现代主义音乐家“无调性音乐”的实践尝试,因为阿多诺坚信勋伯格的尝试奠定了自己现代主义文艺信仰基础和对自然属性见解的表达的同时,动摇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树立起的伪自然主义法则,也让资产阶级调性原则在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无地自容。试图为“无调性音乐”建立理论体系的尝试是和以音乐为武器对抗资产阶级调性原则的实践和左倾音乐立场相对立的。所以他不出意外地极力反对勋伯格的学生们在许多年后试图将“无调性音乐”建成体系化的理论,甚至阿多诺与一些故友因理论上的分歧分道扬镳,就是这样的道理。总体性概念不可能有办法充分表达现实世界个体间的差异,但现实世界的关系又荫蔽在总体性概念中,使个性受到打压,反制了启蒙自身。个性的“质”的不同和世界总体具有的那种非同一性被扫进了同一性规则的圈套。
伴随着同一性概念所带来的主体对客体的极权主义,以及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重置所带来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及异化和物化。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物化简单地理解为主体的客观化,即主体在经过物化这个工序后变得和外物无异。但阿多诺坚持认为真正的物化更复杂。物化不是简单的主体客体化,否则无需用物化替代客观化这一过程。而是物化不仅满足了主体客观化的些许特征,更令客观化后的主体不是像自然之物那样是一个僵死的客体,它应当是流动的。 这与马尔库塞的物化观点不同,马尔库塞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物化理论的核心内容:物化所需克服的“记忆”是外在物的内化 。阿多诺则认为在启蒙时代的个体救赎更为重要,救赎的力量类似于个体对客体的回想,它是“记忆”作为的主体性原则。阿多诺批判了自黑格尔以降就意识到的这种物化理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曾致信本雅明,谈到之所以提出“任何物化都是忘却”不是因为他对黑格尔的赞同。相反,阿多诺是在批判他和他的继承者,批判他们忽略了物化后的主体的复杂矛盾。 物化有极强的排他性,它能笼络和搅乱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达到了消除“异物”的目的。
三
犹太人就是欧洲的“异物”。“二战”的残暴和本雅明的自杀令阿多诺在反对反犹主义的立场上更加坚决,这不仅因为他带有犹太人的基因,也表明“奥斯维辛”的存在正好论证了同一性哲学的死亡特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犹太人是工具理性的极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第一个靶子,反犹主义者亟需破坏作为差异和反抗同一性的犹太人领地,变成待欧洲大陆肃清的异在之物。这样反犹主义让犹太人在欧洲成为社会秩序中当被消除的对象,成为当被破坏和抹除的种族。
反犹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隐秘的支配机制有关。早期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将劳动者支配起来,又用劳动来掩藏这种支配,让每个劳动者在各行其职和糊口的薪水面前变得顺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藏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普通劳动者甚至无法用微薄的薪水糊口,更不用说拥有和资本家相同的购买力。劳动者事实上无法触及权力高层,他们属于两个完全分野的阶级,罢工成为工人最行之有效的对抗方式。至此,资本家必须摆出与劳动者同样的姿态,出现在生产的第一线,或者参与进来。同时,资产阶级必须倡导劳动的光荣,让自己成为奥德修斯那样的象征,也让劳动者成为真正辛勤的劳动者。反犹主义的起源来自作为“遴选对象”的犹太人,把它放到劳动者面前让劳动者注意到这就是让自己变得潦倒贫穷的“那一个”,它身上有用不尽的贪婪欲望。犹太人被作为祭品献祭在理性主义的祭坛上,正应验了阿多诺的论断——在纳粹德国,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神话要素。 犹太人成了这样的种族象征,不是哪一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个群体。
被遴选出来的之所以是犹太人,原因之一是那时直接与劳动者接触的大多是生产关系中流通环节的犹太人,是权力最高层和最底层的中间环节。很久以前,一部分犹太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欧洲大陆,又协助罗马帝国将罗马文明传遍四方。但他们始终被作为不被接纳的无根的民族,生活在皇帝和诸侯的庇护之下。犹太人的遭遇与其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关,使得它一步步变成劳动者指责的对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商人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被仇恨的命运伴随资本主义的传播伸展开来。在犹太教传统中,教义要将信徒引向缺乏的东西,引起人的注意并想办法去填补缺乏。这在犹太人的重商主义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对欧洲大陆的基督徒们来说就截然不同了。到了基督教那里,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它继承了犹太教的某些特质,也极力宣扬平等、救世和爱人等。这些做派使被遴选的犹太人在基督教徒的心目中格格不入,宽容不再有意义,犹太人是欧洲的异教徒。基督徒的盲目性包含了一切,总体性的哲学观念推动了反犹主义的兴起,一无所知的人便被轻易地利用为一切行动的执行者。这如同曾经防抗过的北欧人、吉普赛人、犹太人那样,建立真理标准,来排除不符合真理标准之物。真理的标准内容自然易于编造,因为在近似生理刺激下的民众看来,幌子只是行事的光冕堂皇的理由,要做的只是消除异物。一旦犹太人成为贪婪、欲望、苦痛、异教徒的象征,那么打着的诸如“拯救家庭、祖国、人类”的口号只是帮凶而已。
事实上,欧洲的犹太人是同化了的犹太人,阿多诺把犹太人同化的过程称之为模仿。模仿原来是生物学的用语,意思是生物为了抵御天敌将自身融入周围环境的行为。这种模仿与阿多诺的真理认识基础中的模仿问题是相通的。在社会学方面,可以举出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中不得不被“同化”而生存下来的方式这种拟态的伪装。 反犹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同化的纯洁性,他们还将鼓吹犹太人种族不纯洁将带来的极大危险,犹太人个体强大的持存力量让人不安。受反犹机制控制的民众接受了纯粹的信仰,以希特勒等领袖为精神导师,如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反犹活动,只是信仰的内容不同而已。这时的德国民众被高度提纯,犹太人被极端的理性和同一性哲学做了工具性的、技术性的处理。如观察毒气室的犹太人从精神尖叫到无力反抗再到死亡的整个生理过程,如将犹太人的皮囊作为装饰等等。这种理性是与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将反犹主义者概括为极端偏执人格的人也连同精神分析学一同被扫地出门。
偏执从法西斯领袖那里扩散开来,法西斯主义者试图通过残暴的体制教会民众的残暴,以此维系自身的凝聚力和纯洁,他们认为这将带来恒常的稳固。体制的压抑和人与人的物化激起了个人的支配欲,带有自己种族标签的人会无顾虑地殴打、虐杀带有犹太人标签的人。犹太人越是示弱或显出惊怕的样子,越容易被虐待致死,这是种族间的性虐待心理。因为施暴者的支配欲已经全面开启,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理由去经历眼下却无需理由便能历经的快感。1938年“碎玻璃之夜”发生当晚,住在德国的犹太人被宣布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每个人只能携带一个手提箱携带随行物品。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在家中的一部分财产被纳粹官方占有,另一部分则被他们的邻居夺走。 据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莱尼.瑞芬斯塔尔回忆,希特勒常将宣传看作一种手段,为不同的目的就需要不同的手段。 鉴于笼罩在宣传口径下的犹太人罪行,反犹分子还会把犹太人幻想成真正施暴者,自己夺取对方的财产是实施了正义,杀死对方也是实施了正义。法西斯治下,个体失去了双向反省的能力:不能反省客体和自身。人们不能判断和分辨自己的欲望和体制的欲望,“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 每个人不需要对自己和其他与自己共处的个体负什么责任,只需要为体制的意志负责即可。反犹主义调动起内心的破坏冲动,反叛地维护着关于理性的标准。如前文所说,市民阶层的伦理观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而传播开来。但是,市民伦理赋予市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每个个体更加被动了,最终成为虚妄的理性的载体。反犹主义借助这种压抑和被动,激起了市民的反抗力量,再给予些许官方的承诺和施舍,力量就大得不可估量了。社会世界的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虚假社会身份”背后的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更加体面的社会身份,因为这样能让自己更接近本真或接近社会权力核心。物化的压抑让个体服服帖帖,主观能动性被层层剥离。无论是行善或是作恶,只有任人摆布的份了。
四
“二战”后,西方世界对反犹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思。人们希冀于更温和的关照来实现恒常世界的目的,却又让整个世界陷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消费的境遇里。这一境遇一直延续至今,还将继续延续下去。换言之,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削弱物化的企图被反戈一击了。每个个体拥有的判断和抉择被盲目的统领一切的过程囊括进去,启蒙想要排除的人类早期草率、鲁莽的判断,再一次回到人类面前,这一次它在世界性的后工业过程面前以更无逻辑、更无力反抗的姿态显现。
回顾“二战”结束后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冷战”背景下,反抗资本主义庸俗和暴戾的学生运动伴随着资本垄断、舆论垄断、“婴儿潮”、“越战”进行起来。以阿多诺所处的联邦德国为例,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西德战后恢复的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青年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喷涌感到的不安和不满。青年学生运动的批判重点集中在美国战后物欲膨胀的生活方式鲁莽地闯入西德;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渐消,相反在小资产家庭那里越拉越大;整个社会结构呈现阶梯型,看似富裕了的民众仍然处在梯子低端;借反共、反省法西斯主义的机会加强自身权威,有专制倾向;另外还包括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成了舆论中心等等。 由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控制了战后西德主要的传媒口径,所以学生运动的批判目的被宣传为颠覆目的。对于民众而言,宣传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民众对这样的宣传没有辨别能力,他们不但厌恶学生的行为,也把批判这件事情说的一无是处。一些人注意到战后经济的发展应当倍加珍惜,也惋惜六十年代末的学生没有“二战”的切身体验,害怕动荡的生活重蹈覆辙。批判变得声明狼藉了。战后的这种现象让阿多诺情绪低落,他认为如果在工业社会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批判行为已经为人所不齿,或被官方宣传引导到这般不齿的地步,是很可惜的。这相当于每个个体都成了维护现有“象征政治”的一部分,想要发表批判意见就必须手握权力,如果自己没有手握权力,就不应该批判。战后的另一些人则把批判功能化了。学生运动进行之时,就有人指责青年的批判是激情所驱使,没有“开出济世良方”。 阿多诺认为,市民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启蒙后的市民能通过自身的学习针砭时弊,那里有一套完整的论辩体系。但在战后,特别是在学生运动息歇之后,个体思想不仅不能对立于外在体制的规定,还毫无脱身之法。时而兴起的批判成了妒忌的衍生物,或者真成了“激情的头脑”了。
失去了批判和辨别能力,近半个世纪以来便是文化消费和文化工业大行其道之时。有产者和普罗大众都被卷入混乱的文化语境中。整个社会做了技术化的处理,说话人和受话人都被标准化了一番。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文化的载体,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让文化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文化也成为了一个随处可以张贴的标签。文化工业也都是在这个标签下,依附同样的体制、同样的价值观,用无出其右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被强制地生产,受文化影响的每一个人被强制地接受。更危险的事实是,人们对这种文化工业从一种略带文化洁癖的回避态度,到充斥和包围时的逃避不了,再到直至今日沉湎其中,文化成了文化的等价物。风格化是后工业时代启蒙的一大特征,它直观地影响着我们对音乐、电影、绘画、文学等各方面的审美。以音乐和电影为例,风格化实际上是设立标准的过程。风格化是一种伪装,观众也把自己伪装了起来,最好把脸用最好的伪装盖起来,再考虑其它吧!这样,勋伯格那样的音乐可能不再被大众接受。每一种音乐都需要通过风格的“审查”,才能被冠以“音乐”一词。以好莱坞为主旋律的风格电影更是如此。好莱坞的大多数电影在结构上都有标准,如在电影进行到百分之几时将有高潮、低潮、转折、泪点、笑点等等。它们只是内容上的差异,但认真比对后会发现,一些电影的内容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观众完全有能力猜到故事情节的下一站。电影技术的发展也使控制欲有了发泄的地方,包括控制自然界和他人。尤其是卡通片,让形象化的卡通人物畸变,有现实世界体会不到的新奇,又能让现实世界的人沉醉。如美国动画片《汤姆和杰瑞》,它的喜剧效果在于猫和老鼠的生物链倒置了。汤姆在捉拿杰瑞的过程中,杰瑞被注入了极高的智慧,因而汤姆屡屡受挫。整部卡通片是一个局,设计者将所有元素部局其中。家具的摆放、树木、食物等都恰到好处地放在那儿是为了在某一刻恰到好处地出现。喜剧捉弄的中心在汤姆,他在卡通片中是不死之身,那么它就能被一遍又一遍地捉弄。人格化的施事者也被设置得丰富:杰瑞、斯派克和泰克、翠儿、女主人等。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言,卡通片的这一转向让影像在观众脑海不断产生摩擦,进而瓦解所有人的抵抗能力。生活中需要屡遭重创还爬起来的唐老鸭那样的倒霉鬼,也让观众学会经得起这样那样的考验。 电影成了庇护,电影院成了庇护所,不仅有电影院的逼仄让现代人享受压抑和自虐的刺激,也随电影的愉悦而愉悦、悲伤而悲伤,带来双重感受。阿多诺本人像无法接受新生的音乐那样难以接受新生的电影,他甚至用纳博科夫《洛丽塔》中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观众看电影都闭着眼、长着嘴。” 为了和风格化电影对立,反风格的电影应运而生而生,同时也表达了主流电影意识形态之外的反抗。但反风格电影的结构和情节都和观众的一半观影经验大相径庭,这反而激起观众对它们的兴趣,“反风格”也是观众习惯性地给加上的标签。
工业社会实现了人类的联合,它已然找到了防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从幻想和无意识残忍性那里回忆起的本能欲望的方法。 但是,这样实现的持存是有代价的。没有了“强大的敌人”和“深重的苦难”,就没有了人类表现“勇敢与自由”的对象,只是单调地沉湎在人和社会同一性的幌子下。 尤其在高度发达的大都市里,个人已经不再是自己那个“个人”了,个人意志被社会系统彻底瓦解。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标准化的社会下进行模仿,几乎所有反叛模仿的人都只能做做表面上的工作,诸如穿破洞的裤子、染绿色的头发等。这完全是标准化的衍生品,是夹缝中的人做的偶然个性化了的事,他们没有自立了,只是在身上罩了一个自我安慰的罩子。想要拿到一纸聘书、进出像样的商店、和“社会契约”的朋友会面,就的把罩子取下来。
资产阶级的存在被分割成了商业和私人生活,而私人生活也被分割成了他的公众形象和私下秘密,对这种私下秘密来说,也被分割成暴戾乖张的配偶关系和形影相吊的自我安慰,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纳粹分子,往往把友谊当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与他者的契约关系中,他根本建立不了任何内在联系。这就是文化工业为什么能够成功解决个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到了后来,它也成了社会变得非常脆弱的原因。
这样文化工业泛滥的结果是大众文化对个人的品味提出了挑战,贴有文化标签的“某某”和“某某某”被一同以文化或文化复兴的名义放到了文化集市上,文化被廉价(甚至免费)地消费,低俗又被抬上神坛。民众,尤其是曾经的普罗大众,在变得稍有钱财之后,品味直线下滑,变得粗俗不堪。商品的拜物教不可能协助每一个人在品味问题上做出区分,人们又普遍地失去了明辨能力。消费主义设下以数量取胜的诱惑圈套,铺张和浪费成了文化工业下社会模型的肿瘤。只要触动任何一根和外物连接的神经,每个人的感情都因陈辞滥调的浓厚渲染变得敏感和易碎。
参考文献
[1] [德]西奥多•阿道尔诺. 张峰译. 否定的辩证法[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渠敬东, 曹卫东译.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3]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M]. Trans. Nicholsen Shierry Web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M]. Trans. E.F.N.Jephcott. London: Verso, 2005.
[5] Theodo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M]. Trans. Edmund Jephcott. Palo Alto: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Theodor W. Adorno. "Subject and Object" [C].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London: Continuum, 1983.
[7] T.W.Adorno. On the Problem of Musical Analysis [J]. Music Analysis, 1982, 1
(2), p169-187.
[8] [美]马丁•杰尔. 瞿铁鹏, 张赛美译. 阿多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9] [日]细见和之. 谢海静译. 阿多诺: 非同一性哲学[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德]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 鲁路译. 阿多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1] Yvonne Sherratt. Adorno's Positive Dialect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02.
[12] Christopher Craig Brittain. Adorno and Theology [M]. London: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0.
[13] Robert Hullot-Kentor. Things Beyond Resemblance: on THEODOR W. ADORNO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 [法]德里达等. 郭军, 曹雷雨译. 论瓦尔特•本雅明: 现代性, 寓言和语言的种子[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5]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 程志民译. 理性和革命: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6]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文良文化译. 图腾与禁忌[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7] [德]尼采. 卫茂平译. 偶像的黄昏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8] 张世鹏. 60年代末联邦德国大学生运动 [J]. 国际政治研究, 1989(3): 页28-33.
[19]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M]. London: Verso, 2009.
[20] "Expelled Jews' Dark Outlook" [N]. The Times. 1 November 1938.
[21] [美] 斯蒂文•巴赫. 程淑娟, 王国栋译. 极权制造: 莱尼•瑞芬斯塔尔的一生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22] [古希腊]荷马. 王焕生译. 荷马史诗•奥德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23] [英]罗素. 储智勇译. 权威与个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4] 佚名. 冯国超译注. 山海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5] [西汉]刘安. 顾迁译注. 淮南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6] 方国瑜. 彝族史稿[M].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
-
《启蒙辩证法》读书报告
一、 “辩证”的启蒙:新一轮的神话
作者开篇就提到:“就进步的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其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而知识的本质“在于时间和劳动,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展,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与人类生活”。
而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在通往科学道路上逐渐远离了对事物意义本源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来代替原因和动机。对启蒙后的理性世界而言,仿佛任何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都是幻象罢了。“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而“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它把思想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 。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的是:认识事物不在于单纯的理解、分类和计算,而应该是在于对每一种事物的本质加以实实在在的确定。于是,从感性和神话到理性和知识,从唯灵论的巫术到启蒙后的理性知识及保罗万象的工业技术,人的主体观念逐渐与所要认识的客体相分离,变得越来越独立。在此一过程中,人们用启蒙使知识替代了幻象,但随后又成为了知识的奴仆(即上文所说的工具目的化,对事物的本质探求变成了对作为工具的公式、概率的盲目推敲)。最终,科学和理性主义作为神话之后新的“普遍真理”使人开始对其顶礼膜拜,“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
对自然的一种再现(神话)转向另一种再现(理性)的过程中,人类始终无法脱离自然,甚至越陷越深。而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并接受了从属地位,最重要的是:人们将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了起来。
那么人类不断去“再现”自然、崇拜由此产生的“真理”并且轻易的服从于各种形式相关统治的根本动机或原因何在?书中作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恐惧。要知道,“人是天生寻求安稳的动物”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并未将根源全盘托出。恐惧,对未知之物的恐惧,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贪图安逸的本性之源。为了把握不可知,更好地去操控自身的命运并且排除恐惧,才有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 如此一来,这句话便不难理解,人们对神明与启蒙的崇拜都只是一种试图脱离恐惧而产生的从精神上的慰藉。
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精神上的慰藉是需要现实存在的中介去达成的,这些中介就是神明与科学的秩序及其代理人,简而言之,其背后就是统治。人们被轻易统治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人天生的蒙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就是统治具有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为助人脱离苦海的幸福承诺,众所周知,这些承诺指向的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未来,缺乏理性或者理性有限的人们在这种欺骗之下产生依赖和。最终,大部分人逐渐失去其主体性,在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如行尸走肉般自我持存。
“泛灵论使对象灵魂化,而工业化却将人的灵魂物化。” 作者在这里以启蒙后产生的工业化的世界为例,为我们展现了被统治的人们顺从路径和全部的图景。人从观念到实践行为,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物质与商品生活的洗礼,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和塑造。其中隐藏着的将集体操控化为权力工具的权力,这些统治的力量就是将个体拼凑起来并使其逐步丧失自身主体性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物化甚至是人的异化便油然而生了。“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 这种逻辑有力地解释了社会主体普遍客体化(物质性的异化)、理性成为统治工具的现象。
“生产系统一直规定身体是为社会机构、经济机构、科学机构服务所造就的生产系统,这些机构越是复杂和精致,身体所能得到的经验便越是贫乏。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 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被物质和工业文明俘虏、并被统治的状况是存在着主要路径的,它便是上述提到的理性化的分工劳动及消费者地位的确定性。这种社会角色的确定仿佛是必然的,这也证明了统治者的狡诈及被统治者的软弱。只能按照统治者意愿出卖自身劳动力被统治者,其物化程度越来越高,最终的结果便是:商品至上,人物同化。
“不仅有可能把启蒙的观念刻画成进步的思想,也有可能使它延伸到传说时代的开始。” 启蒙的“辩证”已经昭然若揭:一方面,它终结了先前的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旁若无人的展开了新一轮的统治。
二、神话、启蒙与道德
我们如果稍加了解下《奥德赛》的故事梗概,再结合本书所言,便可以发现:奥德修斯放逐自我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抗拒和背弃自然,他的这种抗争自然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即通过艰辛的返乡历程去摆脱自身相对于自然的虚弱,从而改变命运,做命运的主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奥德修斯有着启蒙者的影子。
伴随着启蒙,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主客体完成了彻底的分离甚至对立;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主体客体化(物化)的情况却司空见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晚期),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普通人而言是势不可挡的,他们或是被蒙蔽或是心甘情愿地越陷越深,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无法自拔。“奥德修斯感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他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他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人必须在欺诈和失败之间做出抉择。” 可见,人们其实除了顺从之外其实已经别无选择。作者在此处还举出了神话故事的例子,用“比蜜还甜的莲子”去比喻资本主义商品物质化的生活所无法替代的诱惑 ,进一步地揭露了启蒙所带来的工业文明无可比拟的威力。
接下来作者提到了启蒙的又一果实,即:科学秩序(理性知识)的高度同一性。理性只有在这种普适体系的同一性下才发挥作用。它具有一种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康德认为存在着“纯粹知性的程式安排”,即在事物的可理解性尚未进入自我以前,知性就已经把这种事物的可理解性作为一种客观性标示出来,就像判断力是有条理经验的“指导准则”一般。那么我们可以说,科学知性在这里已经俨然代替神明秩序成了新的“指导准则”,而这种启蒙的产物是高度同一的,仅仅在技术细节上有所差别。
在这种同一性的至高权威之下,理性中的计算思维成了认识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甚至可以说它将其自身作为认识的唯一路径。任何事物都可以转变成为“一种概念模式的单纯范例。”也就是说,在你对一个事物下判断之前,先验的概念机制就可以决定感觉;启蒙后的人们把世界“先天地假定为他们自己加工制造出来的质料(而这在启蒙前人是由上帝这种人自身对自然的再现物所创造出来的);理性沦为同一性的范畴,它只允许对社会职位加以分工,但是人们作为被统治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角色地位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科学本身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而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启蒙则变成了一种把真理与科学体系等同起来的哲学。”
随后作者便从神话和启蒙中引出了道德的概念。他认为:“理性是计算和筹划的工具,它对于目的来说是中性,它的要素是相互协调……理性变成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因如此,它可以统帅一切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成是筹划的筹划。” 将上述这段话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性本身是无关痛痒的工具,唯有利用理性的目的才是有善恶的价值判断之分的。比如说对那些意欲统御一切的独裁者如法西斯主义者来说,随着其恶的目的暴露(如为了高效率地种族灭绝,采用了毒气室的形式),作为其工具的中性理性也变的好似阴森可怕起来。
“自我持存作为一种天生的欲望,就像其他欲望一样,有着一颗邪恶之心; 但是,注定会对这些欲望发生作用的效率与制度,即独立中介、机关、组织、系统等等,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展现为合理性。” 理性尽管已经表现的助纣为虐一般,但是在人的异化到处充斥着的商品世界中,凡是能体现出经济利益和价值的,便能被称作是合理的。
三、文化工业:一个狡诈的陷阱
“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万事万物皆起源于上帝的意识;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
在启蒙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想的所思考的往往是由看到、听到和认识到的所决定的,而你看到、听到和接受认识到的则恰恰是由文化工业的生产部门决定的。他们的产品包含着两大特征,即:从时间轴来看,产品是预先设计好了的;从空间轴来看,产品是高度同一化甚至重复的。文化输出的商品化使得它得到了致命的异化。简而言之,文化所要解决的已经远远不是人的精神内涵的饥渴需求了,文化工业产品的生产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
那如果有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抗的异议者存在呢?情况是否会有所扭转?
我想答案在书中已经给出,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经典名言:“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却把矛头指向了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必须像我一样思考,否则就割掉你的头;而是说:你可以自由思考,不用像我那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你的,不过,从这一天起,你在我们中间就变成一个陌生人了。”
托克维尔一语中的,秩序的制定者和统治者们所施加在反抗者身上的将是生活物质与精神道德上的双重压力。在物质生活上,如果试图持有以物换物这种原始生活方式,并拒斥一切商品经济的人在物化社会中将无法得到自己生存所需的任何东西;而在精神生活中,“没有工作”就将会被社会集体与“没有能力”和“软弱”画上等号(当然社会集体是指已经被工业文明物化生活驯化了的),从而对反抗者形成排山倒海般得精神压力。
在预设了镇压反抗者的手段之后,工业文化的生产者便坦然自若地设下了陷阱,进一步地欺骗和驯化着无力挣脱的人们。“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 启蒙后逐步建立的工业文化其欺骗大众的面目已经逐渐显现,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浑然不觉而已。
阿道尔诺最后细致地分析了工业文化下的娱乐和作为其目的的快乐。他认为娱乐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实际是劳动的延伸,人们娱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暂时地)劳作的困顿,并以养精蓄锐再次投入到劳动中为最根本的宗旨。而现有的技术资源和设备(如电影)很好地满足了大众不真实的娱乐需求(一如既往,这种娱乐是以满足经济利益需求为目的的),使其深陷“温柔乡”而无法自拔。
“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逃避和私奔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最后总得回来。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它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贴了。” 简单的来说,在启蒙后的文化工业时代,“娱乐”已经被完全异化了,因为其作为目的的快乐对人们而言是明码标价的。而娱乐和快乐在此的真正内涵也已经非常明显,即:防范社会,点头称是。
“工业所关心的就是,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和雇员,事实上,工业已经把整个人类,以至于每个人都变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公式……对雇员来说,他们想到的是合理的组织,而且他们不得不去顺应这种组织;对消费者来说,他们通过电影银幕或专门看在奇闻异事的出版物,可以感受到选择的自由和新奇事物的诱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对象。” 最后,阿道尔诺形象地总结性了工业文明下无可奈何的人们的境遇。
四、反犹主义:病态的偏执
提到了法西斯专政下的反犹主义,作者认为其之所以能如此疯狂的原因便是成功地发动了民众。一战后,在苦难中盲目的战败国民众被别有用心之徒(或者说偏执的理性主义者)利用了自苦难而来的绝望与愤怒,以偏执的、片面的、极端的和道德沦丧的方式将这些怒火全部(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施加到犹太人这群无辜承担莫须有罪名的人身上。从而使得像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从上至下都陷入了疯狂之中。
作者进而分析了民众的盲目性,他从宗教入手,认为“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来说,宗教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替代品。” 人们对耶和华的信仰渐渐转变成对其代理人和由他们定下的教义教规的无条件顺从。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崇拜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只可惜,从希特勒到一般德国民众对反犹主义的认知都是偏执和病态的,这才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
“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基础上的……如果说模仿本身是消防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虚假投射则是把自己等同于周围世界。对于模仿行为而言,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加以遵从的一种模式,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同外在世界混淆在了一处,并把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说成是敌对的东西……在法西斯制度下,这种行为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作是符合现实的;疯狂的制度变成了这个世界现实的合理规范,而对这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反叛都被当成是精神错乱。” 关键还在于,反犹主义者不健全的方面并不在于投射行为本身,关键在于它丧失了关于投射行为的反思能力,它逐渐丧失了反思客体及自身的能力,并最终失去了辨别能力。
简而言之,反犹主义者将幻象等同于真理并加以实践。这种偏执狂般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思考的固步自封当中,它对其自身思想已经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否定性,它固守着得永远是一成不变的病态的判断。其整个思想进程没有去捕捉事物本质,而一以贯之的武断只能反映出其自身思想的软弱无力。
上述这种偏执,就是“认知的黑暗面”,它是由于低级、愚蠢却又致命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反犹主义者试图把所有思想(或者现状)都理解为自有的、少得可怜的经验;同时却又“极力贬低把自己排除在外的精神和经验,并且也把自己排除在外的社会冠之以罪恶致之名。”
作者最终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些一知半解的病态偏执甚至是诸多盲目崇拜形式的方法,那便是教育。但是同时他又对此作出了看似悲观的预见,“一旦教育由于经济原因奄奄一息,就为大众的偏执提供了无数新的条件。”
对于作者最后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局内人又将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 作为最早研究文化产业的著作,感受到作者的预见性和批判的思想。作者担忧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艺术品将更多的体现出经济资本导向的特点,大众的价值取向也将更多的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作者认为交换价值会引起艺术及内在价值的损害,造成商品贸易之外的道德、情感、传统价值的缺失,艺术也成为了资本运行中的娱乐消遣品。贵族精英的艺术文化开始发展为大众的民间文化,美好事物的价值因为资本贸易不能得到体现。从文化产业近些年实际发展上看,其实并不能完全否认工业化制作对文化产业的促进,生产效率与知识含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有工业技术的功劳。流行音乐、电影与电视剧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也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生产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大规模复制从某种程度上同样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
-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个命题: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社会上哪个行业赚钱,资本就会像潮水般涌过去。社会中的资本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它所到之处就会使原来美好的事物遭到贬损,因为它抽离了传统社会中各种内在价值,取而代之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不断扩散,其实就是工具理性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它为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道德的沦丧、“上帝之死”与绝对价值的缺失。《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很清楚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对传统价值所造成的冲击: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
按照传统的观点,尽管资本的洪流无孔不入,但现实中至少还有一块“处女地”是资本未能企及的,那就是艺术领域。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艺术是独立的、非功利的,并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艺术的这些性质使得它能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
但是,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当今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和资本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结合, 取得了一种新的形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的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艺术。首先,新的传播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产生了新的艺术类型——流行音乐、电影与电视剧;其次,大众文化的产生使得艺术的受众变多了,艺术不再为少数人所独享。再有,艺术的生产方式转变了,因为工业社会使得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艺术品的神秘性被抹除了,其价值也降低了。并且,人们对待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由传统“专注凝神的方式”转变为现在“娱乐消遣的方式”,艺术由原来的严肃性逐渐趋向于现在的娱乐性。
而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认为,艺术依附于资本,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因为艺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文化,而社会文化又直接影响大众的意识结构。艺术的堕落造成了社会大众意识的异化,并彻底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下面试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论为例,分析他们的批判理论。
《启蒙辩证法》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个标题说明了两点,第一,文化工业是启蒙后的产物,而再根据《启蒙辩证法》第一部分“启蒙的概念”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出文化工业是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结果。第二,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而文化工业的这种欺骗性则是作者讨论的中心所在。
为什么说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呢?我认为,作者这样说至少包括以下几种涵义。
首先,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并不是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艺术品,而只是伪装的艺术品。或者更直白的说,这些所谓的艺术品只是商品,它们从以生产出来开始就只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它们只具有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没有真正艺术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因而,在文化工业中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则必然要服从市场规律。艺术的生产与传播要依赖于资金和技术,艺术作品乃至艺术家的纯粹性不得不在经济利益面前妥协。甚至有人认为,艺术家已经沦为资本家的雇员。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也都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一过程整合了所有生产要素:从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到最后制作成的音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印在了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过如此。”
艺术与技术和经济纠缠在一起,使得艺术本身的特性荡然无存。“文化工业抛弃艺术那种原来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 按照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理解,“风格是所有艺术作品的保证,而文化工业则抵斥风格。”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实质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只会生产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而观众的艺术品位又会因大众文化的泛滥而普遍低下,他们只懂得欣赏“唐老鸭”而不懂得欣赏“嘉宝”,他们宁愿看小说改编的电影也不愿意看托尔斯泰的原著。“机器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运转。它在决定消费的同时,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东西都当成了风险排除在外。”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生产被消费兴趣所制约,消费兴趣又受限于市场上流行的产品。如此一来,社会中并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艺术品的商品化造成的必然结构就是艺术品的标准化,市场上所兜售的文化消费品其实质都是一个模子制出来的。人们看到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多样性是虚假的多样性,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所产生的幻觉” 。
艺术品作为审美客体,它存在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审美主体——人对其接受方式的转变。人在对待传统艺术品的方式是凝视与欣赏,在这种审美方式上,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已经将人的主体性消解殆尽:
“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联系;然而,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 ”
为什么文化工业有如此魔力呢?可以从以下几点稍作分析。
首先,大众在各种文化消费品面前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而文化工业的固有特征造成的。作者以电影为例进行分析,由于电影是连续播放的,具有持续性,所以“电影观赏者不想漏掉情节,则不能保持持续的思想。” 电影的特性使电影剥夺了观众的思考权力。这样,电影就可以随意扭曲或者控制观众的意识,“一切都来自意识……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都是制造商中的意识来的。”而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对观众意识的控制,恰恰就是文化工业的谎言本质。“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因为文化工业颠倒了大众对真实的认识,“外部世界被当成是电影经验的连续,真实世界与电影分不开了……电影强迫他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真实。”
艺术作品的传统使命是促发人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使人能对生活、社会现实有一种深刻的体察。而当传统的严肃艺术被轻松艺术所取代后,情况就大不一样。艺术成了娱乐,人们将艺术当成了繁忙工作后的一种消遣,“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换来的短暂快乐在作者看来却是虚假的幸福,是资本主义失意者对现实的逃避方式。文化工业创造的各种无聊的喜剧与卡通固然容易逗人发笑,然而,“排解的笑声是摆脱权力的笑声……用屈从恐惧的办法来解除恐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样的笑声是一种对幸福的伪装,真正的幸福并不需要笑声,真正严肃的艺术作品也并不包含笑声,正如“勃莱德尔与荷尔德林都没有多少幽默感……在虚假的社会里,笑声是一种疾病。” 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依靠这种幽默、诙谐的文化得到巩固,人们沉溺其中,对自己的真实的悲惨状况漠然不知。就这样,本该具有的批判意识被顺从意识所替代,人们在享受各种文化乐趣的同时,不知不觉间就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
正如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书中写道:
“ 在这个可以控制温度的地方(电影院),城市里的失业者可以找到冬暖夏凉的感觉。然而,不论电影院有多大,这些言过其实的生活机制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尊严。那种“完全利用”现有技术资源和设备来满足大众审美消费的想法,正是构成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经济制度却从来不肯利用资源去消除饥饿。”
由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水泥”。这也就说说,文化工业的初现加固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的垄断,继而彻底控制了人的意识。传统艺术的批判性维度业已消失,当代艺术是堕落的,腐朽的艺术,是彻头彻尾地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 - G•B•克莱登曾在其《两性史》中预言,今后社会将会彻底摆脱两性这一陈旧的二元结构,而代替以一种崭新的一体性构造,即攻受构造。无独有偶的是,著名心理学家威廉•施密特也在其《社会变态心理学新编》中指出,攻受结构已然成为当代社会的标准心理模型。1988年哈桑国际心理学-社会学年会上,多位知名学者提交了相应的报告。此种新结构对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今天,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启蒙的批评者们也同样为我们揭示了一种特殊的辩证法,即攻受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包含三个方面:1,启蒙批判者是攻,启蒙是受;2,在启蒙批判者的批判中,启蒙是攻,社会是受;3,现实中,往往社会是攻,启蒙批判者是受。
所以需要立即指出并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攻与受并不是对特殊性取向的嘲讽,也不是要贬低社会、启蒙、启蒙批判者中的任何一方,更不是要暗示此间的某种失败,即便有人认为我们有理由说,至少就现实生活而言,此间确实存在着失败者。由于按照哲学传统,现实往往意味着廉价、庸俗、卑下,因而攻受辩证法既然牵扯到所谓的现实,自然也就是一种品位低劣的人身攻击。但这只是在拾启蒙批判者之牙慧而已。攻受辩证法正是要深入到启蒙批判者的批判背后,去揭示这一批判的真意。因而无论启蒙批判者自身如何看待启蒙与社会,或者现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既然我们用辩证法来称呼这一新生事物,那么自然就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三个要点中,哪一个是正题,哪一个反题,哪一个又是合题?答案很简单,很明显它们之间并不是正、反、合的关系,所谓的攻受辩证法也不是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三一式辩证法。它即拒斥黑格尔式的絮絮叨叨,也反对马克思式的胡言乱语。它是一种乍现,一种浑然天成的非文本,一种正、反、合的后一体式同一性。这三者的整体就既是正题,也是反题,更是合题。反过来说,这也正为我们揭示了何以我们必须采用攻与受这样的非概念式语词。如果说启蒙现代性离不开肯定,而反启蒙离不开否定,那么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们不得不永远陷于一种卡拉特菲式反神经焦虑症,一种攻与受的非主奴式的、后神经元发射的、阿普洛意识场割裂型的反同一性自我定位。正如菲尼斯堡皇家学院1994年特里尼实验小组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无非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普遍心理癔症,一种超时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前所述,这一结构正是攻受辩证法所要揭示,一种超伦理性的返身容受体。
对于攻受辩证法的这一特殊形式,批判者可能指责其为结构主义的建构式模仿,是一种修辞上的现代主义谎言,是对反启蒙大师的中产阶级诠释,而无疑,此种诠释是启蒙神话的产物,是一种无生气的符号映射,预示着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全面胜利。或者,有人也会指责,攻受辩证法是一种后弗洛伊德式的谵妄,正如同启蒙自称要对一切存在做一番精神分析一样,攻受辩证法也妄图用现代精神病理学将反启蒙者作为仅剩的疯癫症加以迫害。在启蒙的祛魅中,一切非理性都成为了睹灵者的噩梦。然而启蒙者并未意识到,启蒙理性恰恰是非理性,真正的睹灵者恰恰是这些所谓的精神分析大师,而他们所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正是现代性所演绎的各种光怪陆离。启蒙丝毫没有消灭神话,启蒙造就了更多的神话噩梦。
对于这样的指责,我们无需过多辩解,只需要指出,攻受辩证法既不是什么结构主义的幼稚语言,也不是什么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叙事,更与中产阶级的自慰式谄媚或新古典主义性具崇拜式精神分析毫无关系。攻受辩证法所真正要做的,乃是在存在论上对反启蒙者、启蒙、社会等等之间的普洛透斯式扭结做出后现象学的澄明,用一种非文学批判的后古典反思意识对其先验语法与后设语言进行全面关照。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揭示其内在,即非反讽性的反讽。
当然,感受这一辩证法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为工具,来解读如《启蒙辩证法》这样的知名反启蒙著作,及其作者。不难想象,批判者又会将此种实践冠以“后实用主义意淫”之名。正如同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所谓的实用主义大加鞭笞一样,看来此种实践也不得不担负起各类光怪陆离的实用主义形式的恶名。然而诚如晚期希腊哲人阿伽通所说的那样,任何哲学都必须担负起一切反哲学的恶名。既然我们已经指出,攻受辩证法乃是一种非反讽性的反讽,因而自然也就能够既排斥又容受此种恶名,正如同前面我们的驳斥一样,此处的批判也只是一种源自分脑式精神盲视症的非意识性梦呓。
比如,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笔下,启蒙以间歇性神经质的纯粹性清除了鬼魅及其派生物,但自身却成为了新世界中的古典式鬼魅,其宗教就是反灵魂、反精神的物化教。然而有趣的是,通过阅读《启蒙辩证法》,我们不难发现,此种幡然领悟式的启示语言却似乎暗示着一种反畏惧式的精神恐慌,仿佛在期待一种总体性的聚集,一种威慑性的监控。透过攻受辩证法,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揭示为一种当今时代每时每刻都不断爆发的后泛灵论式扭曲,一种因饱受总体性肆虐而导致的自由交换式无能为力。不管是作者们的观念,还是他们笔下的罪行,抑或是所有这一切妄图折射的人之真正本性,都不过是现实主义的幌子,是隐身在古往今来各种神明、宗教、性妄想背后的史前异化权力的扭结面具。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操控,因而我们在《启蒙辩证法》及其作者身上所能找到的,无论是文本性的还是非文本性的,符号性的还是非符号性的,性具崇拜式的还是非性具崇拜式的,都只是一种攻与受的蛮荒呻吟。
无疑,要人们接受攻受辩证法,接受它所揭示的无情事实,都还有很大的难度,就好比前面提到的那次哈桑大会上,共计27名学者愤然离席,而特里尼小组报告至今仍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式伪科学,1999年又有全球81位哲学家联名反对卢森堡授予斯特纳•普莱利•哈维林国家人文学院荣誉院士头衔,要知道正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攻受辩证法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相信,攻受辩证法所遭遇的这诸多磨难本身也恰恰证明了其真理性,我们所目睹的这一切,归根到底也终不过是攻与受的无限轮回,或者借用前面的话,一种西西弗式的蛮荒呻吟。 - 这本书对我来说的确太早了一点,因为它竟然算是我社会理论方面的启蒙读物。只是蛮讽刺的是,作者是本着批判启蒙去的。书很难,记得我最开始读的时候,连读几页一句话都没读懂:连字面意思都不懂。后来放了一阵,我用自己的话把第一章“启蒙的概念”重述了一遍,才算是有了点头绪。贴一篇自己的presentatio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nd its Aporias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why and in what sense does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rove to be aporetic?” And my presentation today will be based on three articles listed below:
Reason, Utop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lbrecht Wellmer
Modernity and the Aporias of Critical Theory Seyla Benhabib
The Entwinement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 Re-Reading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Jurgen Habermas
It is without dispute that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written by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for reasons here I will not attempt an analysis of the Critical Theory as a whole) has seen an assimilation of Weber’s concept of rationalization into a Marxist framework. Largely this unison could be seen to have resulted from the rise of Nazi regime which has been taken as a regression of humanity. Theoretically, this book has encountered aporias which for sure could be explained, to my own understanding, only withi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ut intellectually speaking, the aporias faced by it could not be fully understood only withi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y presentation would be only focused on the former and to see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ir efforts of this great project.
1. The acceptance of Weberian concept of modernity means that The Frankfurt School has already found itself in this fragmenting process of western rationalization. Indeed, considering from the Dark Age in which this book has born, calling for a restoration of real reason is urged just as the call for the doom of Nazi. However, reason, under the rationalization, inevitably differentiated into three distinct value spheres simply resists a reunion of itself. For Weber, this fatefulness is beyond doubt. Instrumental reason or in Weber’s term, purposive rationality strongly refuses to reflect on itself. Nevertheless, Horkeheimer has introduced back the objective reason, which is the ancient cosmological view comprising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Realization of this cosmological view which is a strictly Hellenic sense calls for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utonomy, which could only happen in a society with coherence and solidarity. But this attempt of introducing back the objective reason has found itself powerles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for this process has already shattered down all the categories and needs of past time. Therefore even the very idea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become obsolete. Or put it in another way, the very idea of objective reason fails to find itself understood with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and even by itself. Here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hat Adorno and Horkheimer have tried in this book is not a restoration of objective reason, for this kind of attempt by “which the absolute becomes a means and a scheme for the subjective reason” is undoubtedly against their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This means, therefore, this theory has to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tools of this very same reason, perpetrates the very structure of domination it condemns.” (Benhabib, 1994:119) And this is the first aporia this project has encountered and it’s also the first moment the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has run against itself. Then how to understand their stand or how to understand this conscious adoption while definitely a rej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zation? Logically, when this critique itself has been cursed by which it criticizes, there is no way out. However, since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reason is still valid within this theory (for sure it perhaps only in this theory and none), to salvage itself, the authors have set to locate this objective reason within the dreadful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To understand this, the focus 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aesthetics, to which Adorno have contributed his greatest effort.
2. For Adorno, art possesses the redemptive ability. To explain this, I would like to give a review of Weber’s concept of rational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According to Weber, rationalization happens with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downfall of religion. I want to emphasize here that this is not quite like the sunrise and sunset but in a sense it means a conscious rejection of religious world views. This rejection, which has been constantly intensifying itself alo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has greatly changed our civilization. This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which takes place respectively in culture, society and personality and it brings about:
1) a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e into three distinct value spheres: science, morality/law and aesthetics
2)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economy and the state: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3) methodical lifestyle
It is the very autonomy which art has gain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 while its remoteness to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science tinges itself with a colour of emancipation. This aesthetic rationality is the last bastion which instrumental reason has never completely conquered. In the chapter I and II of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he authors have used the famous scene of Homeric Odyssey, in which Odysseus with his fellow men have passed where the Sirens live. The story tells us that Siren’s song, though otherworldly beautiful and intoxicat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no one could resist them to listen to it less. That means they will ultimately throw themselves into the sea. But Odysseus has to pass but he wants to hear that sweet voice because he’s curious. And so he asks his men to tight him to the mast. Moreover Odysseus has plugged the ears of his men with wax so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hear Sirens’ voice. Here, Sirens embody the dark forces of nature. But they are the art in essence as well. The curiosity for the divine beauty of Sirens’ song embodies the aesthetic rationality indeed. Contrary to the instrumental reason, aesthetic reason works differently. For Adorno,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as identifying and repressing while the latter is entirely non-conceptual but synthetic. Therefore, art could 1) “through the configuration of its elements…reveal the irrational and false character of existing reality and 2) prefigure an order of reconciliation.” (Wellmer, 1991:140) Follow this logic, art could 1) sublat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ia its mimetic function and then 2) illuminate the reality in the light of reconciliation. But whether this aesthetic rationality could really succeed in challenging Weber’s purposive rationality remains problematic. Again, Adorno and Horkheimer have acknowledged this weakness of art and that is why they have forged another concept “Culture Industry” to defend art’s original potential for authentic emancipation. But since art remains only a medium of reconciliation, it’s not reconciliation per se. A medium is what integrates the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But art as a medium could achieve in replacing the language and money (the latter is perhaps the stark reality of our time) or not is questionable. This is the second aporia of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 think from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dustry, one can already sense the powerlessness of art in front of economy. Although Adorno has relentlessly stuck to the dichotomy of “high art” and “low art” which again reminds us or objective reason and subjective reason, this effort remains sadly abstract.
3. This book,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s a powerful testimony of our fateful time, for it anatomizes itself to show the weakness of critique of society. This intellectual experiment is what Habermas has called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which the authors are certainly aware of. Moreover, they even intentionally push it to the extreme and keep it unresolved. (Habermas, 1994:42) And only in this moment, the so-called pessimism, which is often applied to describe this theory make sense. But unlike Nietzsche who replaces reason with power, Adorno and Horkheimer still try to seek hope from the hopeless. Then now,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remained. Exactly how much truth does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has spoke out about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even human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Is our civilization really a plight? And it is very much genuine to say: even everything is beyond certainty but at least we are very much sure that every one might have their own image of modernity. This value freedom is always taken as self-evident. And this is what makes antagonism last and every one would be the potential victim.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but unfortunately this is the truth. Of course, Adorno and Horkheimer in no means suggested a restoration or even returning to the past. But this proces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zation needs a self-reflection to combat its self-reflexivity. And this is what the title of this book actually means.
其实整本书的核心是讲启蒙的self-reflexivity及其悲剧后果。因为启蒙曾经是作为对抗那些“mythic powers”而开始的。但是两位作者暗示说其实这些mythic powers没有被彻底清除,而会在特定的时候重新浮出水面。法西斯就是一个好的佐证。而因此启蒙被工具理性占据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这些自相矛盾的时刻,但是它确并不会对自己做出反省,仍然毫不顾忌地继续”前行“。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种停步甚至是倒退。当然人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这对我们很重要吗?我觉得只要antagonism继续存在,我在上面也说了: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第二,工具理性如何可以反省自身?那么这就不是单靠理论可以去完成的了。哈贝马斯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很多社会理论家大概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用这种哲学式的方法去把握这个问题有其非常大的优点在于这个问题可以被固定住而不同于一些志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那样到最后有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这也是批判理论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不讲实践。当然,我觉得这个批评一点都不靠谱。如今,理论哪个时候这么酷地声称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反正这本书完成了它的使命,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
- 在我们生存的时代,大众文化已经如微尘般每时每刻地漂浮在周遭的空气里。我们沉浸在大众文化中,更多的时候已经对它熟视无睹。然而,就在一片昏昏然中,作为消费品的大众文化竟反客为主,成为驾驭人类理性的工具。
多数大众对此或许是不屑一顾的,但欺骗的神话正在真实地上演。无情揭露这一切的,是德国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纲领性著作,尽管艰涩难懂,但其中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文化价值的批判反思理应值得每一个人都明白。
《启蒙辩证法》的核心观点,存在于“神话即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逻辑中。欧洲启蒙主义认为,人类通过动用理性、掌握技术,最终可以摆脱束缚、树立自我,即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取代因袭主义的宗教神话和迷信。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是对此最好的阐释。但这一切的美好设想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沦为了悲剧的乌托邦:启蒙的初衷在于摆脱神话,最后竟异化为新一轮的神话,继续着对人类的统治。
作为传播学的爱好者,我更关注的是技术理性的异化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在《启蒙辩证法》中,作者将“文化工业”作为被异化了的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就是指一种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量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人类需要娱乐,娱乐大众的文化存在本身并无罪恶,但这背后的种种欺骗让娱乐最终成为神话。
对于眼下文化产业化的大行其道,我始终是持审慎态度的,因为这似乎正验证着文化工业理论。市场化的生产模式追求效率和利益,文化的本质属性会不可避免地被冲蚀,取而代之的是由复制技术带来的标准化与齐一性。同时,产业化的背后是不可避免的丛林法则,最终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垄断,都会使“技术合理性异化为支配合理性本身”。最后,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人类主体性将逐渐黯淡,我们将在声光电影的刺激与欺骗中痛并快乐着死去。
这一切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一切正在真实地上演。
仅以最熟悉的央视春晚而言,节目年年不同,但背后的意识形态却千篇一律——永远是歌舞升平,永远是幸福团圆,永远是赵本山东北俗文化的“傻乐主义”……民族意识建构的背后是文化工业的欺骗,安于享乐的同时是逃避对现实恶劣思想的反抗。
文化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根源于人自身思想的懒惰,最终才由大众文化的欺骗蜕变为自我欺骗。但在文化产业化与全球化蔓延的今天,如果在思想上继续逃避现实、安于享乐,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预言将更加真实呈现。
- O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by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primarily provides a thorough self-critique of the revisionist version of enlightenment by enlightenment itself. In this short essay, I will focus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some main points in this book and then try to relate a few of them to my final project for this class.
From my understanding, the title of this book—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can be generally interpreted as two meanings. First, as is stated in the seemingly self-contradictory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myth and enlightenment, the problematic enlightenment neither disenchants the myth nor empowers human beings to conquer the fears through the mastery of unknown nature. Instead, it becomes intertwined with the dangerous tenets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mathematical calculability. Guided by these tenets, mobile human beings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immobile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self-preservation by the means of giving up their critical thought and original history. In this way, enlightenment finally regresses into mimesis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revival of the myth in its obscured and justified form,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reemerging myth serves as a shelter of violence. Second, the critique of the deviant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enlightenment should be totally thrown awa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this book, however, is in the hope of rescuing progressive insights embedded in enlightenment.
Moreover, by describing this book as a “thorough” critique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essay, I want to highlight the examination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widely tied with technology, history, and the abuse of power manifested as racial/class domination. The first criticism in the aspect of technology mainly targets at the fetishism of technology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By locating this criticism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studies, the authors wage a war against the universal, mechanical, and objectivistic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pointing out the mistake of false projection which projects the inner human mind towards the outside unknown nature. This kind of interpretation is believed to close up people’s creative minds, unify their reactions, and let the outside ideologies think for them. The second criticism is against the contingent history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which is formulated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influence of dominant power, machinery,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e contingent history erases the original memory of subjectivity, rationalizes people’s adaptation to nature in front of the fearful forces and even collaborates with violence to justify their collective actions of oppression towards the unprotected. The third criticism of the abused power is chiefly elaborated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the horrendous exclusion of Jews. Anti-Semitic behavior is unleashed in a rational way in which Jewish people are tortured after they are shaped by the forces of blinded enlightenment and deprived of their subjectiviti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book to my research project, I find the arguments about “stupidity” very useful for analyzing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the official ideologies on Chinese women. Stupidity refers to the status of human mind in which creative thinking is void and only neutral knowledge is left. For China’s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that on social science, the content of social reality analysis is extremely lacked. In this sense, the more educated consciousness lags behind the ever-changed social reality, the more consciousness succumbs to the boring, meaningless repetition. The present order of life which is bounded by the imperfect education does not allow people to work out intellectual thoughts. Especially for women, they cannot even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y of being well educated as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do. As a result,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women are very likely to adopt the official discourses which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subjectivities.
- 与本雅明相比,我更加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如前篇报告所述,我并不完全赞同本雅明的灵光论点,我认为本雅明的理论过多着墨于佐证其艺术政治化理论,及对法西斯主义战争美学的攻击,相对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现象的分析更为鞭辟入里。
虽然在文中不乏见到启蒙辩证法对于文化工业前景的过于悲观性,但其中对于电影、广播和杂志创造的愚民循环系统,以及社会权力已由此创造的绝对统治性,至今仍能适用;对大众文化带给人群及艺术创造者的局限与绝望,以及人尽皆知的暴力的公开化,一针见血的提出,并表示因为其系统设计之完美的毫无抵抗力,宣告其悲叹,而面对即便是如此有思想深度的学者都无能为力的悲叹,阅读完本文之后,更令人感到唏嘘不已。
对于这意识与生活的控制,体制的不可破坏性,是世人自懂事以来便须面对的真象,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或是个人的消极抵抗,都是对此一箝制做积极反抗,但我们总能轻易的见到数不尽的失败案例,使我们更清楚,螺丝对机器的抵抗无异是以卵击石,个人或小群体对体制的抵抗,只会被嘲为愚昧无知;我们没有抵抗的本钱,有抵抗基础的财团或是权力者,则懂得良好的运用体制机械,更加巩固自己的目的或利益;在体制中被开放的呐喊空间,只是被创造的宣泄管道,经过有效控制的管道,能够更好的完成对群众的情感净化,因此我们珍惜虚假的自由,学会顺应时势而生存,对于创造力与生命力被使用价值定义的无可奈何,麻木的被广告洗脑,让意识型态遮蔽我们自身,逃避最后一丝的反抗观念。
对于失去人生目的而生活,成为社会训练出来的同一复制品,最终在体制中获得胜利的人,也许是唯一能够改变与破坏体制的存在。只是有多少这样的人能够在得到操控体制权之后,放弃其所擅长的技俩,破坏其生存的优势基础,重新启蒙大众,解构技术导向的工业环境,将其所背叛的理想重新拾回,而不会再建立新的体制。如此行为与思想的悖论,是我尚不能厘清的。
- “權力”,我想是阿多諾在“文化工業”一詞背後隱藏的關鍵字。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一章的開篇他即提到,文化工業使作為獨立個體的人屈服與他的對手:資本主義的絕對權力。“文化工業”意味著權力,誰控制了文化工業,誰就擁有權力。而這種權力滋生了意識形態,是極權主義,更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因此,“文化工業”本質上就絕非一個中性辭彙,在阿多諾看來,這個詞,是藝術與技術、藝術與資本主義、藝術與絕對權力、意識與意識形態結合的怪物。它生來就註定是可恥與醜陋的,是個資本主義的畸形兒。
文化工業產生暴力。根本途徑是資本主義與當代媒介技術的發展。而在阿多諾看來,文化工業進一步加速了大眾的啟蒙運動,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造成了知識的普遍化。在這個意義上,人人都是知道分子,來到資本主義時代,人們才徹底擺脫了蒙昧。但另一方面,這種充分的文化民主化過程其實是最深刻的暴力,人們掌握著同一種知識,接收著同一種意見,看似百家爭鳴的知識界但背後隱藏的是一樣的邏輯。而這種一致性邏輯,在我看來,就是對資本、權力與技術的絕對信服與崇拜。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技術充分發達的社會中,權力通過媒體,對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可以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在喬治奧威爾的《1984》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這幅未來極權主義在思想控制方面的圖景。
而本雅明與阿多諾產生共謀之處,即在於對這種技術作用(從攝影術到簽字印刷術再到電影藝術)的充分肯定。他們都意識到,是技術改變了生活世界的一切。但與阿多諾不同的是,他對這種新型文化——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背後所抱持的意識形態色彩並不太以為然。
這是個有趣的對比,兩人都從“技術”這一核心概念出發,卻得出了兩個不同的結論。本雅明是個美學家,而阿多諾是個批判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阿多諾是個結構主義者,而本雅明則是個本質主義者。為什麼阿多諾看到文化工業的那麼多弊病,在我看來,是因為他將這種文化放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中去考察,這種文化的實際效果與輻射半徑。而本雅明,儘管也提到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可能會與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共謀關係,但僅僅止於某種或然性描述,法西斯主義並非必然的結果。本雅明從各藝術種類本身來考察,在這種意義上,藝術作品背後的意識形態與暴力,就都成為夢幻泡影。
在全球化浪潮席捲的今天,文化全球化是個頗具爭議分量的辭彙,這個詞是否具有合法性?可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抵擋,以資本與技術為靠山的異族文化入侵?我想,這是我所關切的問題。
- 九零年左右出生的人成长于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之下:先是日本动漫的风靡,再到平民偶像的崛起,最后是当今网络文化的全面普及。七八十年代的由知识分子主导的诗意生活与民主热情已在一次激昂而又成为禁忌的副歌中随风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渗透全社会的,从大学生到初中辍学者都欣然接受并乐于其中的大众文艺。身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我感受的是,真正的文化与艺术是被记载在泛黄书页上渐被遗忘的过去,而今日的传媒甚至图书则更近似于装饰着缤纷色彩的空盒子,一种买椟还珠,一种被利用而不是被欣赏的文艺。
这样的一种文化以至社会境况在四十年代的美国就已出现。当是时,资本主义绚丽而靡靡的火焰燃烧着二战时相对和平的北美大陆。然而在侥幸与狂欢之中,在霓虹与歌舞背后,也已经有一批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与批判。1944年成书的《启蒙辩证法》就是两位思考者对启蒙的堕落现状的斗争檄文。其中的《文化工业》一章,则是针对当时的大众文艺,也可以说,是针对我们当前的大众文艺。
在他们的批判中,有两点令我深有感触。一是大众文艺的庸俗性。尼采说过一句话,“原来属于上帝,后来属于贵族,而今属于庸人”,这用来描述文艺的命运再合适不过。启蒙运动作为人文主义的倡导者,试图唤醒被宗教权威和集权制度蒙蔽了千年的人类文明之光,这当然具有伟大的意义。而此时涌现出的大批文艺精英,将辉煌的业绩永远铭刻在人类的历史上。但这一运动在两个世纪之后的文艺大众化时代却走入了歧途。如果能不失文艺的内涵,则普及文艺本是一件幸事。可是现实却是,我们在扩张文艺的受众与创造者时的过分包容已令文艺丧失了其本色,丧失了其超越性与批判性,成为了娱乐的玩物,商业的工具。文艺本是凌驾于社会现象之上而对社会进行审视和训导的高尚之物,如今却沦到社会中层甚至底层之中,失去了其清香的花冠,而被迫披上了小丑的戏装。如此之文艺,有不如无。
文艺为何会有如此的遭遇?这涉及的是书中谈及的另一个问题,即大众文艺属于大众只是一种表象,而其实质是虚伪的——背后藏着资本的操纵。文艺属于上帝的时代我们只能瞻仰,文艺属于贵族的时代依托于少数天赋头脑中的灵感闪现,而文艺属于庸人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文艺维持与发展的基础竟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与经济运动规律,变成了商人的利欲与大众的虚荣心。文艺,是铜臭的傀儡,是俗人的装饰品。它满足的不再是人类的兴趣与责任感,而是贪婪的腰包与空虚的灵魂。资本用精致的技术与严密的计算制造了文艺,并假惺惺的与大众分享,甚至邀请他们一同创作。不过这有个不容缺少的前提——记得买票。大众自以为是文艺的选择者,是所谓的“业余爱好者”。他们为自己的品味与时尚沾沾自喜,却不知其实自己一直置身资本所指定的规则之下,越是热衷于这种文艺,越是想以它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越是深陷规则之中。伽达默尔说过,不是游戏者在玩游戏,而是游戏在玩游戏者;只有放弃了目的意识和紧张情绪,游戏者才能真正的成为游戏的主体。今日的文艺界与此很是类似。摆脱了虚荣与盲目追求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文艺光鲜迷人的外貌,而是它的千篇一律与苍白乏味,以及暗藏在它身后的得意数钱的手指与手指主人狡黠的偷笑。
我们不得不给这样的“文艺”加上引号。当然,我们也不能将社会上一切文艺加以贬低,也不能完全无视商业操纵下的文艺中含有的一些实在的价值。我们所希望的,是更多人能对自身的处境有更深的认识,用批判的超越的眼光和态度面对文艺以及这个社会本身。
- 法兰克福学派的顶梁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主张用“文化工业”来代替“大众文化”来表示现代大众传媒及其传播的流行文化。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市场上销售可以替代的项目被生产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精神需要。概括而言,文化工业这个批判性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商业利润的文化商品,使大众的闲暇时间变为另一种可以被剥削的劳动;其二,文化工业具有浓厚的而隐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量,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是一种控制变得更加密不透风,使社会统治秩序变得更加坚固的“社会水泥”。这个概念暗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表明其只不过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产物。
我今晚和一位好朋友吃饭,她的经历让我再一次验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伟大之处--远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就对它有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性认识。我朋友在为一家演艺公司工作,主要内容是作为导演的助理,承接各种大型晚会和演出。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大众传媒体制极其特征。
我国目前是完全的国有的有限的商业运作体系机制。基本特点是:
一是,完全依赖政府领导,由政府任命国家媒介的领导,政府决定其工作方针,负责部分的经费来源(历史上是大部分,现在是小部分);而是,政府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宣传党政和政府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职责;三是,节目通常严肃呆板,以新闻评论和教育节目为主(改革开放前的特点,现在已经是在把重点放在了娱乐)。
中央电视台便是现行媒介体制的最好代表,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它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机构,以至于那些畏惧中央电视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企业,不得不舍得血本,巨额投标广告,以至于中央电视台赚得钵满盆溢。2008年,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曾报道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竞价排名制度使得一些虚假医院和医药公司产品能够通过网络销售大量非法药品。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广大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大家似乎能从这种节目中获得一种快感,那是夹杂仇富、狂热、发泄的情感。百度的竞价排名制度怎么能让一些虚假公司榜上有名呢?这不是坑害百姓么?中央电视台这个时候似乎成了他们间接行使权利的工具。那是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因为长期被奴役被压迫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权力行使欲望。这种快感使得大众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大众媒介的“社会水泥”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大众不自觉当中已经放弃了抵抗,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的任务。同时,当大众在家满足于欣赏娱乐节目的时候,电视媒介其实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了广告。换句话说,电视媒介不仅收我们的有线电视费用,还把广告引入家门。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把大众的闲暇时间变成了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虽然这种定义本身充满了偏激和极端,但是它却人震惊,原来这就是本质。
回到刚才,什么叫虚假广告?为什么竞价排名就有错?请问,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后面的广告不是竞价而来的?请问中央电视台的脑白金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当年《南方周末》因揭露脑白金的虚假成分,史玉柱连夜从深圳飞往广州想阻止《南方周末》刊登,但是遭到了拒绝。而央视,难道在刊登一条广告时有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尤其可耻的是,央视曾经报道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问题。请问央视播出这种广告是不是一种“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百度作为中国互联网的老大,尽管在网络上有着无限风光,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政治力量抗衡上和央视简直不在同一个档次。央视可以对任何一家企业进行揭露,但是没有谁能掀起抵制央视的浪潮。唐骏来小礼堂讲座时曾经谈到,在中国企业家最需要的不是经济知识,而是政治敏感度。2009年的春节晚会,不出所料,我们看到了百度对春晚进行的赞助。很多人没有了解到这个细节,稍微仔细想想,百度需要做广告吗?可是我们可爱的文清主持人在主持的最后一句都会加上“此次活动得到电子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支持”。原因是什么?以下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央视对百度说“看你小子最近赚得比我还多诶,怎样,做几个广告如何?”百度一头雾水,“我干嘛上你做广告?你做你的电视,我做我的网络,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央视恨恨而归,于是一出百度虚假广告的节目出来了。百度被打了一巴掌,还吃了个哑巴亏,有苦难言,只好乖乖交钱。央视尝到了甜头,把目标对准了Google。谷歌毕竟是外企,不喑国情,又被爆涉嫌宣传淫秽网站。当然,无论是虚假药品,还是宣传淫秽网站,这都是两家互联网公司对技术的控制不当,或者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他们得到的惩罚无可厚非,可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央视这种无赖式的敲诈。净化社会环境仅仅是其中一个小目的,更大的其中的经济讹诈。不信,你再用百度和谷歌搜索“激情,成人”等关键词,你觉得就没有了吗?你认为央视还会继续追究么?
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体制指的是媒介为国家所有,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又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得广告利润,而后者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政治结构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经营支撑媒介再生产。简要而言,就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要求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权力寻租成为常态。从央视著名导演赵安落马,到央视记者受贿,无一不都在用权力到市场寻找租金,无一不在讲述一个恒古不变的事实:权力和金钱的勾结。
未完待续
- 启蒙的意义在于真实的世界不再于有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是永恒,永恒的事物不仅不会朽坏,还会生根发芽,还会有来生。
- 启蒙的意义在于没有自己的天空时,创造一个天空于一个世界中。存在于一个世界的本质,不在自身,而在来世。来世的意义有依存于世界的来生,神的威严,没有解婆。结构主义不是没有根源的,他来源于自身的动力。没有真实的世界就是启蒙。结构主义的根源在于元素论和辩证法。真正的自己。
- 一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人都把自己的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黑暗”的中世纪并非黑暗。但试图考量其之所以被称为黑暗的标准,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都是以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之标准来看待所谓的中世纪的“黑暗”;而问题则在于这样的一种标准,所谓的科学的、理性的标准从何处而来呢?
从现今来看,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已经似乎是如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那样地划分明确的了;但是,追溯西方思想之源头,科学与哲学仍然是不能或难以形成其明确概念的。当我们去看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著作,我们会看到有《修辞学》、《物理学》、《诗学》、《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形而上学》、《工具论》、《范畴篇•解释篇》……看着这些名目,试问从现今之语言语境中,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的总体学问称之为科学呢?还是哲学呢?
由于自身学养之浅薄,无法去考察科学一次的词源及其原始意义,但仅凭自己的那点不成熟的知识与记忆来看,科学与哲学相对地表现出一种理性、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地扩张,用波普尔的观点就是在于那一种可证伪性。科学就是对人的理性高呼万岁,如同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科学中的常态观念就是一种进步的观念,而这些观念精神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可以说所谓科学的真正出现在于西方近代的启蒙时代的开端,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真正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理想的伟大,甚至无所不能。科学在启蒙时代真正走上发展之路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是启蒙真的对于人类而言是进步的吗?在读了法兰克福学派之鼻祖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1]后,自己仍然对其中的思想一知半解,但也试图从中谈谈对启蒙的新理解、新认识,也由此谈谈自己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个庞大问题的一些小看法。
二
什么是启蒙?康德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P.1)这种自主,我们就以理解为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充分依靠自己的个人的理性,这便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有了这样一种科学,我们就能改变并支配自然。
而这样的一种科学“既不听从造物主之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P.2),这就是知识的伟大:“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知识的真正的目的、范围和职责,并不在于任何貌似有理的、令人愉悦的、充满敬畏的和让人钦慕的言论,或某些能够带来启发的论证,而是在于时间和劳动,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P.2-3)
启蒙的目的在于开化人类,并用一种现在我们认为是科学精神的理性来替代古代中世纪以降的一种幻想,是要唤醒世界;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P.1)“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P.2)“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原因只被当作衡量科学批判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或许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继续为科学批判提供参照的古老观念,是创造性原则的最后一个世俗化形式。”(P.3)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命题在科学中已经是荡然无存,被科学所抛弃。
但是我们又奇怪地发现,科学却一直抓住过去的一个命题而死死不放。“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却发现了某种古老力量,并且对普遍的真理要求顶礼膜拜。”(P.4)科学永远追寻着哪一种普遍真理而去;而这种普遍真理体现在这样一种普遍科学之中,在那里,“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实事,事物被简化为物质。”(P.4)“数学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谕多质。”(P.5)
一切自然变成了客观性。在启蒙了的人面前,一切对他而言的课题好似成为了科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主宰。”(P.5)这种统治自然的科学精神同上帝统治自然在意义上是相似的,所以霍克海默会认为“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前言,P.5)“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P.6)科学追求的是自然的普遍性,于是“科学中不再具有特定的替代物……他代物变成了普遍的可替代性……正是因为实用科学的这种区分很是随意,每个事物都划入到同类物质之中,于是,科学的对象变得僵化了;正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其他事物整齐划一起来,先前那种一成不变的仪式都似乎变得灵活多变起来。”(P.7)
这种神话是否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哲学?这已是很难限定,或许在远古时期神话巫术于哲学史别无二致的,但是从霍克海默的上述论述中基本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这样一种启蒙的科学精神并不使人进入到真正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所谓的这样一种近代以来的进步的启蒙精神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得到了彰显。科学剥夺了自然的多样性与特性,使一切多成为他的客体,并寻求其中的普遍真理。科学用抽象作为工具把每一件事都解释为必然规律性的再现,而这种原则实际上也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
科学的精神在于把握事物的普遍同一,“人们通常喜欢把概念说成是所把握之物的同一性的特征,然而,概念由始以来都是辩证思维的产物。在辩证思维中,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P.11)“特别是在概念与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关系中,形而上学的辩解暴露出了社会现状的不公正性。公正的科学预言已经无所作为,它丧失了任何表达手段,身下的只是一些中性的符号。这样的中性特征,甚至比形而上学还要形而上学。”(P.17)
同样,科学也带来恐惧,使个人异化,工业化将人的灵魂物化了。“个人知识把自己设立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P.22)“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及启德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P.23)
科学最终导致德使个人对丧失自我的恐惧。人类走向一条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算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样使得统治者更有利于统治,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P.28)“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思想本身也只能被迫在命令和服从之间做出选择。”(P.31)
所以科学的启蒙到底带来了什么?所谓的进步却带来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并不是进步的失败,而恰恰正是进步的成功。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P.28)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是在述说这样的一种辩证法:所谓的启蒙的科学只是过去神话的巫术而已。
三
那这样一种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述引用并行文的过程中已经略回答了这一问题,也就是对于科学,仍然需要哲学地批判。从中我们就可以管窥科学与哲学的一点关系了,对上述科学的一切的批判都应是哲学的。而下面的文字则是自己的另一些引申想法;仅作余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给与这样的一个启示:作者是讲对于一切的批判纳入了哲学的范畴当中来了。康德的名言是: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而在我看来一切批判都是哲学的,批判是事物的一种自省,一种自我反思,而一旦任何一事物开始进入一种自我意识的反思的境地,则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上了。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只有到了哲学地自我批判的境界,才能说是成熟的。所以,哲学作为一种批判,一直是万物似乎走到穷途末路时的一线曙光。
但在当时这并不为哲学家们所认同,从19世纪开始科学主义日渐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哲学家们自以为哲学走到了穷途末路,在这种悲观心态存在的同时,又产生出另一种心态:就是似乎要和科学一争主体性地位的那样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对自我否定的反抗,还不如说是自卑心理的自负表现。
这种自负表现在之后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上:
一条是向科学的靠拢: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最好不过的例子。哲学也想要变成一种科学,之后像英美分析哲学,弗雷格和罗素提出一种逻辑语言,想把解决哲学问题变成想解决数学问题一样,这种逻辑哲学也是向科学靠拢。又比如狄尔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概念,胡塞尔最终希望建立的一种科学现象学的目标等。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发展路径给这一条道路以大大的问号:维特根斯坦自以为《逻辑哲学引论》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因为他把哲学问题归结到了规范的逻辑语言中,可说的都说清楚,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但当他重返剑桥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为之一变了。
另一条是仍然特立独行:当海德格尔重新把“存在”的问题提到了哲学的议题上来时,使得一切其他的哲学都黯然失色。过去认为已经是走进黑洞的本体论,在海德格尔那里又重新焕发了它的光辉。这不得不让人认为,“存在”这一主题永远存在,并永远属于哲学,而正是可以仰仗此,让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
而这两条道路却体现的是同一种心态:即一种爱哲学的心态。当科学成为主流之时,哲学家提出哲学也是可以有科学的精神,这是一类爱哲学的表现;而如另一类人与科学坚决决裂,追求哲学之伟大独特性时,这时另一类爱哲学的表现。在面对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家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拯救哲学的道路:一条是“你有我也有”的追求普遍性的道路,科学所体现的精神哲学同样可以;另一条是“我有你没有”的追求特殊性的道路,科学与哲学不是一回事。甚至对于一切事物的批判都应依靠哲学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是爱哲学的心态。
科学与哲学就存在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以科学为视角来爱哲学的这种心态所体现的两条道路的选择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胜利了,因为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不曾有过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更不会有,科学的地位到如今已是不可动摇。但《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及其它所有的哲学家们给了我们以一个更高更阔的视野看待问题,这便是哲学的永不会消逝的对人类的贡献了。
注释:
[1]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下文之所引用皆出自这个版本,就直接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2]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版,第23页。
- 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的名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及受其深厚影响的现代社会之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欧陆战争后与第三国际式的马列主义分道扬镳。作为一个放弃了直接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独裁的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亦没有走向伯恩斯坦所代表的康德式修正主义,而是从学术的立场在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下(本雅明认为革命是一种末世性的救赎,而阿尔多诺则认为它是一个有取向性的憧憬)冷眼观察和批判工业化、都市化、和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却又不甘于只做学术,认为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开的,以“批判理论”此名来形容他们对社会实践其思想的理念。
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归根结底来说是失败的。启蒙运动代表了魔法社会(玛娜)与科学社会的分界线。科学社会的根本理论是工具理性:其宗旨是把所有的事物和关联性都减小为最低限度的形成体,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工具以用之。而不能被简化为最低限度形成体的现象则被忽略。社会的单位变为了个体:架于个体之上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则就此失去了意义。在其客观性了解世界的同时,启蒙理性物化了世界。个体虽然存在,却无法保留其主体性;集体虽然存在,却无法解释集体行动(praxis):启蒙理性是无法从主观和相对的角度出发来了解世界的。启蒙辩证法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辩证法来说明启蒙理性的种种问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眼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性思想最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甚至法西斯主义。
《启蒙辩证法》选择了《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来代表启蒙理性的锥形。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提到,奥德修斯可以在其本人不在的二十年时一样让其王国正常运行。牧户和佃户照常工作,王后虽然名义上代表了王权却并没有执行任何权力——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奥德修斯对与其飘扬地中海的士兵水手的控制也是绝对的。面对海妖歌声的诱惑,奥德修斯命令其手下堵住耳朵,不受影响。而对于自己他的要求则相反。作为启蒙理性的代理人他需要对证明和享受自己权力带来的果实:所以他要受到诱惑,要享受海妖的歌声。但同时启蒙理性的代言人却不是自由的。他在定义自己的权力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工具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部分——欲望。所以他要求部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直到船离开海妖所在的领域为止。那末,奥德修斯在遭遇海妖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弊病。一方面其根本是控制,另一方面其本质是压抑。在奥德修斯听到海妖歌声却不能离开的狂喜和痛苦中,代表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人类最早的记载中展现了身影。
诚然,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比喻并非完全合理。将一近代现象追溯到远古史诗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忽略了历史性特征的做法。而且奥德修斯作为一英雄人物其本身既是大于凡人的;他的英雄式意志并不能和普世性的启蒙理性相比。作为一个多元性的个体(polutropon/ man of many turns),奥德修斯并不是一个只有理性和运用理性去看待世界的。他并不只把一切事物都简化成可以测量和控制的变量,而是保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虽然知道他的性格会导致他马上将再次踏上旅途,虽然知道伊萨卡并不能给他带来一切,奥德修斯还是义无反顾地一点一点地朝着他的家乡走去。这种精神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所批判的启蒙理性所不必备的,也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相反的“魔法社会”的朝圣。
http://decennis.com/ruoshuitang/2008/03/11/%e5%90%af%e8%92%99%e8%be%a9%e8%af%81%e6%b3%95%e4%b8%8e%e5%a5%a5%e5%be%b7%e4%bf%ae%e6%96%af/ -
仔细把三篇主要的文章和附录一再读了一遍。振聋发聩。敏锐到我有时候都怀疑是不是译者自己把当代的问题写进了书里,而不是两位作者在上个世纪初写的。
阿多诺担心的问题跟本雅明是一样的,都是对主体客观化深刻的恐惧。但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凸显出阿多诺为人熟知的反同一性理论。对于文化工业的解决之道,更明确地表现于阿多诺试图通过“模仿”而达到和解。通过概念超越概念。尽管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取消他所警惕的理性。
从现在来看,工业、文化、教育的模式也都是创造消费需求,而不是满足需求,是模式化主体的典型,相较20世纪初毫无改观变本加厉。人在摆脱自然的同时内心更渴望返回自然,然而,返回自然?ok,会有更多的商业模式来帮助陷入到回归自然的阻碍之中。
尽管这种批判模式只能提供模糊的解救之途,维尔默也指出过,审美合理性是理性的一部分,与技术理性、制度理性不可分割,更无法完全取代后两者,但是审美的超越是在实践理性的明晰之前,比较好的解救之道。
发现我还是读的太少太零碎,要抓紧积累。
-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阿多诺是最早完整提出文化工业思考的思想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具体说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主义肆虐全球,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自主的声音,个人的主体性终结了.由于采取了合理化的生产方法和新的控制群众和暴力镇压的方法,熟练的,受教育的工人阶级被摧毁了.正因如此,政治经济上的极权主义可以说成了阿多诺思考文化工业的起点.阿多诺看到了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大众欺骗的启蒙,并未起到一种对人的生存环境及模式的批判,从而更好的促进人的生存发展,获得崭新品质的作用.反之,文化工业从一开始就以整合一切思想,同化做为个体的人为目的.他将整个知识和文化统一起来,取消其实质内核,用量来衡量一切.在此种情况下,阿多诺认为人类沉沦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与上述纳粹主义对人民的控制有着某种相近的意义.所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同二战以来的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集权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如同纳粹主义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一样,文化工业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以商品拜物教作为其意识形态,穿着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假外衣,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形式对大众的思想进行管制,只不过这种管制用娱乐和享受性取代了以前的强制性。比起以往的强制管制,文化工业的控制更能取消大众思考的独立性,抹平大众思想的差异性,使所有的一切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利也迅速膨胀起来….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文化被加之以商品资本意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距离在消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常常混为一谈,真实生活与电影再也分不开了。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在生产的类型。 最重要的是,文化工业取消了大众反思否定的能力,使他们认同并依存现有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自身来说 ,任何特殊的观念,现在都不过是一种极端抽象的概念: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呲呲牙 、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 文化工业利用细节变化、风格变化的欺骗手段,并于权利阶层意识形态勾结,一步步的取消了人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性的思考,从而达到其整合一切、以普遍代替特殊的目的。
一、在阿多诺看来,在文化工业产生以前,人们能对事物进行独立自主的感知和思考,消费者能自主选择需要的消费品,其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方式和内容。在那时,高雅艺术能保持其自律性,并与通俗文化自觉区分开来。而文化工业预先决定了消费者需要感知的内容,生产出符合权力阶层经济效益的商品,消费者不再是主体,而成了实在的客体。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均已被预先设计好了。消费者所要做的仅仅只是按照文化工业设计好的程式进行消费。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电影、电视以及以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上。以好莱坞为例,制片商、投资方、监制、导演构成了一组强大的权力机制,他们直接决定着受众能看到何种题材,何种风格,何种内容的影片。而层层审查制度早已保证了最终供应影片的“合法性”。当然,表面上看来,公众有选择观看何种影片的权利,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为了使公众顺顺当当地接受业已规定好的标准而做出的掩护。同样,广播更是打着民主的幌子“使所有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所有人都被纳入到了真伪难辨的“业余爱好者”的范围之中,而且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文化工业的统治下,个人已经不能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慨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了,文化工业剥夺了个人的这种思考能力。“事实上,社会权利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商业机构也拥有着这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力量”对消费者来说,他们的消费意识均被预先设定好了,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电影明星和肥皂剧都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即使消费者认为它们具有形式内容或是风格的不同,那也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细节的不同.难掩其总体上的例行性、统一性。细节的不同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那即是:大众文化总是以客体的身份适应作为主体的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而阿多诺却在《启蒙辩证法》中一针见血的道出了这种细节变化的欺骗性质。他在文化工业批判部分的第二节写道“细节是可以变的,在流行歌曲中,比较短的见奏可以产生某种效果,英雄突然间产生的失态,情人从男明星那里所受的粗暴对待,以及男明星对倍受宠爱的女继承人的藐视,所有这些细节,都象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能够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只要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受到惩罚,谁会被人们忘却,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 这一段描述清清楚楚的说明了细节虽然变化无穷,但预先设定好的整体是必然与细节无关的。每一个特定的情节,每一段音律的跳跃,每一节插科打诨都不过只是所有事件的总和。通过这样的手段,文化工业用其思想成功取代了大众的独立思考。实现了其整合之路的第一步。
二、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工业的整合之路,阿多诺用“文化工业的风格”作了更深入的阐述。透过其阐述,揭示出了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不过是对大众的一种安抚和哄骗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大众个性化的要求,使其获得一种虚假满足感。而多样化风格的幕后操纵实际是对压抑一切、削平一切的我们无法逃避的权利的回声。
阿多诺指出现今时代,各种所谓的风格远比19世纪以前名目繁多。“中世纪的建筑家们在仔细研究教堂窗户和雕塑的主题时,绝对不会像制片厂的某些机构在最终确定选题之前,对巴尔扎克和雨果的作品进行检查那样苛刻。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在根据更仁爱的神圣教义的规定,来决定让罪孽深重的人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苦难时,也绝对不会像蹩脚史诗的杜撰者在计算英雄究竟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或者是小姐的裙边究竟要提到什么样的确切高度等问题时那样细致”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消费者的选择性增多了,个性化和创造性也大大优于前时代。这对满足大众追求独创性和新颖性的心理无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从而顺利实现了文化工业诱使消费者按照它设定流行模式进行行为活动的野心,取代其思考,将其行为牢牢的局限在对制造商有利的范围之内。正因有此假象,所以对风格的追求愈演愈烈,以致人们不能接受没有风格的事物,“人们很容易接受不遵照32节拍或第9音域的规定而写成的流行歌曲,而不接受那些包涵最慎密的旋律或和声细节、却没有独特风格的流行歌曲…明星和导演必须很“自然”地生产出具有一定技术特点的风格”风格的细分使受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自己选择的独特风格的产品是为自己量身订造的,于是对这种多样化的风格产生一种认同感。文化工业便顺理成章的达到其以普遍代替特殊的整合一切的目的。因为尽管风格表面上千差万别,实质上却是千篇一律。所谓的差别仅仅只是为文化工业扼杀个性而涂上的一层保护色。这层保护色使人们丧失个性而浑然不知,他们盲目的追寻流行的脚步,寻觅时尚的步伐,将其本应具备的反思、质疑、批判精神抛诸脑后。文化工业取得了胜利的制高点。阿多诺清醒的看到了风格的虚假性质,他认识到“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这揭示出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实际上是用普遍取代了特殊。“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调和,规范与特定的需求之间的调和以及惟独能够为风格提供本质的、有意义的内容的成就,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连所有对立两极之间最微弱的紧张状态都消除掉了:这些相互协调的极端状态软弱无力的统一了起来;普遍替代了特殊,或者相反。”事实上,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在风格上玩花招,而是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伟大的艺术家不可能把风格完美无暇的展现出来,而是把风格作为一种否定性的真理,用来反对那些用极其混乱的方式来表现痛苦的做法。文化工业却与其背道而驰,走了极端。他取消了事物真正重要的内容,仅仅只留下风格。使同一性和标准性完全操纵了大众意识。使其批判意识有了被根除的危险。于是,文化的发展不但不能达到使人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获得新品质的目的。反而使人安于现状,丧失个性,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文化的危机。所以阿多诺称文化工业是一种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因为启蒙已经背离了其初衷,遭遇到了遗失。启蒙的本质本是对人之存在进行一种永恒的批判活动,大众文化使启蒙丧失了它批判的、怀疑的本质,反而成了奴役束缚人的工具。
三、单单只是上述两方面,阿多诺认为还不足以说明文化工业对大众的独立意识、批判精神进行整合。文化工业要想真正取得牢固支配地位,就必须设法使大众自愿随其步伐行进。在这一点上,文化工业在大众身上找到了对其有利的突破口。那就是利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来满足大众追求享乐与快感的心理。为此,“文化工业保留了娱乐的成分”通过娱乐建立它对消费者的影响。文化工业竭力承诺它能带给大众快乐,使其身心愉悦。做出这种承诺的方式则是物化一切,整个社会成了一台生产物质的巨大机器。在此过程中“艺术抛弃了自己的自主性,把自己完全与需求等同起来,它以欺骗为手段,彻底剥夺了人们摆脱效用原则的可能性”。高雅艺术面对物化世界彻底败下阵来,艺术彻底远离了艺术价值和主体价值,完全成了一种满足短暂、虚假需要的消费品,这使文化工业成功将它与商品进行了整合。艺术家的创造也成为了赚钱的手段。以致于贝多芬一边愤怒的抛开司各特的小说,怒斥其写作只是为了赚钱,转过头便毫不留情的将自己最后一部四重奏扔掉,因为市场不接受这种类型的作品。所以阿多诺嘲讽的称贝多芬为老练、倔强的生意人。连贝多芬这样的艺术家都不能免俗,可见物化已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通通被交换价值所取代“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地方,到处充满着走马观花和确凿可靠的知识:沽名钓誉者取代了鉴赏家。消费变成了快乐工业的意识形态…人们仅从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切事物:有用的观念可以用来衡量一切,而不管它是不是模糊的任何客体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价值”如前所述,物化使人们不断的生产出物质,且不间断的消耗着物质,通过提供各式商品,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与消耗欲,使其得到了一种虚假的满足。无论消耗是物质商品还是精神商品,文化工业都能使消费者的得到一种快感,消费物质成了一种物质、享受。它造就了虚假幸福感,从而压抑了反思。针对文化工业物化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快感,阿多诺有这样的论断“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权利与彻底丧失权力之间的对立”最初人们追求消费是为了从繁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放松。文化工业却利用人们寻求放松的心理,合时宜的制造出快乐工业。各种流行音乐肆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变革”:调式的随意组合;古典与现代、抒情与摇滚、通俗与民族胡乱结合。似乎花样翻新得越快就越能实现其带给消费者快乐的承诺。在大荧幕上,更是充斥着血腥暴力镜头、情爱画面。对消费者的感官进行冲击,工具理性的的膨胀使技术与电影结合,产生三维电影、立体电影,益发刺激着消费者的神经,使他们产生虚假快感。连曾经的净土卡通片也变成了展现暴力的场地。以前的卡通片总是能唤起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情感,现在的卡通片“从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动机,整部影片的播放过程就变成了不断破坏这个动机的过程:观众最想看的,就是把主角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暴力攻击的对象。这样,有组织的娱乐就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过程。”阿多诺认为,这些让人吃惊的情节使影片实际成了毫无意义的垃圾,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瓦解人们的所有反思,让消费者相信这样的欺骗是一种快感,从而变得服服帖贴,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受到了文化工业牢牢的控制。
当然,我们还需看到,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整合、欺骗作用,常常与国家意识形态勾结在一起,形成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文化工业取消大众的主题性,消除其反抗意识正是垄断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可将文化工业看作国家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文化领域每一次变动其背后均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电影业上。尽管电影可用不同方式表现不同的主题,但具体什么内容能呈现给受众却必须经过严密的审查制度的检验。审查制度的存在保证了电影宣扬的至少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更多时侯,权利阶层会利用电影来保证其意识形态的实施,各式各样的主旋律电影即为典型代表。通过灌输意识形态,权利阶层将控制人民的缰绳牢牢控制在手中。正因如此,笔者文章一开始变阐明了极权主义是阿多诺思考文化工业的起点。
四、结语:综观阿多诺的整个文化工业批判部分。可见其坚决的批判精神与悲观情绪。其笔下的文化工业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意识遭遇到了整合,个人主体性遭到了剥夺。高雅艺术与商品遭到了整合。真正的艺术丧失了其质的规定性。形式化和标准化统辖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表面上看来具有个性的事物,其实只有细节的变化,目的是为了蒙蔽视听。阿多诺尖锐的批判文化工业是一种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因为他认为启蒙本应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释,应该对人传统的生存模式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创造性转换,促进全新主体的形成,到了发达工业社会,启蒙理性却丧失了其批判精神,蜕化成了技术理性。在此种情况下,晚期资本主义巨大的物质财富造成大众享乐的心理,追求易消化,不用费神思考的事物。文化工业便大行其道,批量生产出大量模式化的物资,并与权利阶层的意识形态狼狈为奸,向人们承诺以快感,取消人们思考的独立性,压制人们的反思精神,防止其构想出另一种幸福生活。大众因此丧失了个性,抛弃了批判精神。这样看来,阿多诺似乎宣扬了一种末世理论。
笔者认为,尽管《启蒙辩证法》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的总体基调尽管是悲观的,但阿多诺还是在最后的《笔记与札记》部分暗示给了我们抵抗极权统治下,文化工业对人的同一化的希望。那即是:依靠自然。他提到“只有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的真实面目以后,自然才能成为生存对和平的渴望,成为这样一种意识:即它从一开始就激励着人们,毫不动摇的与领袖和他的集团展开一场较量”。这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暗示:人被文化工业的同一性从自然的状态中剥离出来了,所以要反抗文化工业,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然的力量。只有回归自然,人才能重建其主体性,使其情感、智力方面的能力都能得到发挥。启蒙也才能回复到其真正的本质上去。所以笔者并不认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阿多诺对发达工业时代的文化工业充满绝望情绪的观点。
- 文化产业就是文化与资本的矛盾组合体。
- 写的很流畅,读起来很舒服。观点有些许片面,值得商榷。我的阅读感觉是,作者对资本主义一词带有明显的“坏的”意识形态叙述,会给另一种相反制度(或许不存在)做某种理论上的虚假支撑。资本一词带有明显的繁殖重复性,已经成为一种通识,其对各个知识领域的侵蚀,迅捷而让人感觉无措。但我们不能认为资本推动下的消费的弊端,就停止消费。消费给我们带来某种主体思维的衰竭的同时,也在创造更多的自由思维的空间。用消费消解权力控制,保卫社会共同体,也许是一种良方。
- 不是“作者对资本主义一词带有明显的‘坏的’意识形态叙述,”而是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等等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绝望的结论。
- 消极与绝望是某种主观价值感觉,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做到价值中立的,你对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的理论理解的知识前见决定了你眼中的绝望,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绝望。如果该理论真是绝望的,我想启蒙辩证法也就不会赢得如此高的荣誉了。之所以被理论界认可,在于其真知之中的希望,艺术和哲学在辩证中获得新生。
- 从另一条路径看,时代带来信息、虚拟社交的繁盛的同时,一种普遍的幻觉能力或者说想象力,这一文化创作的强生产力也在渐渐衰竭
- @猫君眼中有条河 请好好读读原文吧~
- 很有趣的一个方向·
- ls教我情何以堪啊
- 很有意思的文~~~
- 早在史前时代 阴阳辩证法 的雏形就是 雄雌辩证
- GTY老师玩的太脱了。。。
- 寫的太他媽糟了吧
- 您是说哪个?
- 都糟吧……我和阿多諾
- 霍克海默呢
- 一路貨色
說實在的
他們這一路浪漫派觀點真的已經……有點過時了吧 - 這文章是刪節版…………後面我還有一大段,以“張冠中同學提出一個問題”為開頭,就沒好意思放上去!
- 否則我沒有講標准化問題!
- ……非常感谢
我觉得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很不错的,挺敬业 - 是的 那股滿腔的熱血很好!
而且那種對理性的批判其實也很紅了 - 额 我在法国的考试 就是考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 文化产业
- 很导演这样的文章,对于现在的我。
喜欢用自己的语言说清楚的文章。总是引用。
这些概念自己好好想想就出来了。书总要的观看方式是用来翻的。 - 谁能告诉我这本书,和资本统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啥关系。。。。。
- 明显没看懂原书,打回重读。
- 启蒙辩证法不是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的。。而是溯源到古希腊传统把整个西方理性化过程看做启蒙的。。。。
- 看到你的文章,我发现我自己读得更少。
- 阿多诺晚年的时候自己就对早期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同了大众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说他对文化工业充满绝望情绪确实不准确
- 刚看了前言,基本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主题:“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作者在前言中对启蒙的简要看法,简直深得我心,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自己的想法比较模糊,没有他们那么明晰的思维思路。呵呵,绝对是本好书。得好好看看。
- 文化就是思想暴力
- 这是你论文??
- 什么是这里说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