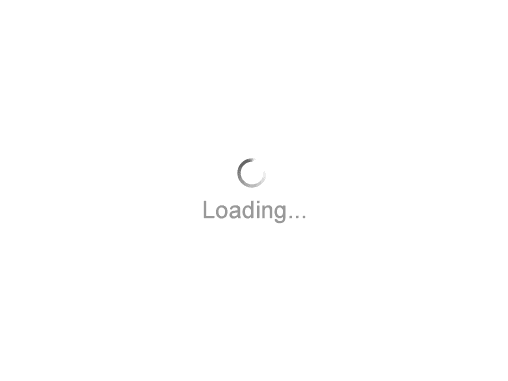立憲時刻
出版时间:2012-2-3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高全喜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在南北和議、《清帝遜位詔書》頒佈之前,清帝國之疆域大有分崩離析的解體之勢。正是在此存亡危機之關頭,清王室能夠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實,屈辱而光榮地退位,將一個偌大的帝國疆域連同他們對於清王室的忠誠、臣服,和平轉讓於中華民國,從而為現代中國的構建,為這個未來中國的領土疆域之完整和鞏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此,現代中國的立國基礎不單純是辛亥革命那種激進主義的立憲精神。它的另一個精神基礎體現在《清帝遜位詔書》之中。遜位詔書雖不是一個形式完備的憲法文本,但它總結和承載了晚清以來若干次或被動或主動的改良立憲運動,有效地節制了革命激進主義的潮流,彌合了革命造成的歷史裂痕。可以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清帝遜位詔書》,共同構成和發揮了現代民國的憲法精神。
作者简介
高全喜
1962年生,中國江蘇徐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政治哲學和憲政理論。著有《理心之間——朱熹與陸九淵 的理學》(1992)、《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哈耶克的法律與憲政思想》(2004)、《休謨的政治哲學》(2004)、《論相互承認的法權——〈精神 現象學〉研究兩篇》(2005)、《何種政治?誰之現代性?》(2007)、《現代政制五論》(2008)、《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論現時代的政法及其他》(2009)等。
书籍目录
目錄
前言
中華民國肇始之憲法創制
《清帝遜位詔書》的憲制背景
《臨時約法》的憲法短板
革命建國問題
人民制憲問題
從《十九信條》到《清帝遜位詔書》
《清帝遜位詔書》釋義
《清帝遜位詔書》之頒佈
《清帝遜位詔書》之憲法價值
「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袁世凱條款」與帝制復辟
三個優待條件及憲法與文化蘊含
《清帝遜位詔書》語境下的「中華人民」
古今變局中的「天命流轉」
後記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55条)
- 这本书具体的内容不分析了,只说下整体感觉,因为内容真不值得分析。
如果说清末民国初年这些文献资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价值。
不光是逊位诏书,清末的一些官员的奏章和文章都很有价值,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情况。
这次的逊位诏书由张謇起草,袁世凯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此二人的思想对逊位诏书的撰写有一定影响。诏书反映的是当时的统治者的心态和当时的社会思潮。张謇作为清末状元,而且主张实业救国,他的既能了解清廷的心态,也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因此,虽然发挥空间有限,逊位诏书还是反映了大部分社会中上层民众的思想的。但这应该是就是其全部的价值了。
本来作者可以有更好的研究方向,即结合逊位诏书及当时许多改革的文件资料、奏折、报刊,分析一下中国实行宪政的可能性,以及宪政建设中对中国传统可能的的吸收借鉴等。这些对于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也会十分有助益,因为这一块恰恰是现在的研究所欠缺的。在这方面,当时的清朝官员如沈家本等都有很不错的分析。可惜作者只是囿于退位诏书,为了能配上论题的宏大背景,只能是对诏书进行无限的无根据的拔高。最后甚至开始耍无赖,认为退位诏书本身也不算什么,要看到背后的历史精神。到这一步,已经完全没有辩驳的必要了。因为这等于说学术不依靠文献资料,要靠人去体会精神。这就不叫学术了,叫巫术。即使是巫术,都属于最简单的:信则有。 - 2011年,时值武昌首义一百周年,发生于辛亥年间那段被后世称作为“革命”的故事,借助某种弥漫在当世的气氛而备受关注。不过对于这场以推翻满清政权为主旨的革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通常都习惯从革命党人的视角出发来作事后的观察与阐发,却在无意间忽视了“革命对象”——满清最高统治者的反应。如此缺失,多半是由狭隘革命史观的宣传所致。所幸伴随着近年来学界突破意识形态樊篱的努力,众多历史资料浮出水面,有关辛亥革命的主流叙事话语早已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辛亥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武昌起义的爆发虽具有偶然性,但在其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那股谋求变革的力量却是强大且由来已久的。面对看似突如其来的变化,清皇室作出的最后抉择是: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份诏书的确意义非凡,它所昭示的古今之变,乃是迥异于之前的任何朝代的,因此无论如何都应当被视为现代中国政治基石的一部分。
也许正是有感于此,更有感于这份文件长期以来的不受重视,在政治哲学和宪政研究领域里颇富声誉的高全喜教授在今年春节一气呵成,写下《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对这份“末世”诏书的宪法意义作了深度阐释,用作者的话说,是“为它唱一首挽歌,作为辛亥百年的别一种纪念”。
恕我孤陋寡闻,读到此书时已近年末。此时人们对于辛亥百年纪念的关注,如同这个世代里任何吸引眼球的事务一样——来得快,去也得快——已经差不多不留痕迹地消散在了公众的视野里。正是于这寂寞中的细细揣摩,让我得以深切体会到了“挽歌”一词所蕴含的悲凉。
不同于大多数学术书籍的论述模式,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直截了当提出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革命的漂泊机制”问题。这一点其实可以看作是全书的核心命题之一。盖因中华民国得以建立,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便是革命。“革命建国”不仅是革命党人理念的体现,在当时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但“娜拉出走以后”的命题,在二十世纪革命话语兴起之后的岁月里,曾经并且至今依然困扰着无数人。作为后来者,作者在检阅了百年中国的历史遭遇后作出的回答是:革命之后,应当尽快制订能够对革命本身起到制衡作用的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使宪法尽早成为“革命之轭”,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因革命激情导致的过度暴力。正是在这里,《清帝逊位诏书》的作用凸现了出来,作者认为它恰恰是革命后制定的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效力的重要文件之一(另一部文件是《临时约法》)。与此相关联的是,被《清帝逊位诏书》所承认了的辛亥革命的性质,作者将其定义为一场“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 of revolution)。运用这一有点拗口的概念,意在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是受到宪法制衡的一场革命,具有反对无限度革命暴力的性质,但它本质上完全不同于那些反对革新国家政制的保守的反革命力量,因而它是“革命的”。唯其如此,才可以被称为“革命的反革命”。
作者将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清朝统治者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视作为宪法性法律文件,显然如他自己所说,是在试图梳理出两条不同的建国路径:一条以革命建国,一条以宪政立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条路径的拥护者,都认同政制需要鼎革的观点。这两条路径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中间历经庚子之变、晚清新政等重重历史关口,绝非积一日之功而成。在最少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为代表的清廷上层中的改革力量,分别从不同方向上推进清末社会各个领域堪称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发挥了合力,最终促成民国的建立和上述两个文件的颁布,使得1911年的那次易帜没有采取传统的大规模暴力的方式,而是南北议和,达成妥协,南方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权力交于袁世凯,北方的清廷和平逊位,由此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整合与彻底革新。这种“合力”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清帝逊位诏书》这份最重要的文件,恰恰是由身为前清状元的立宪派领袖之一张謇代清廷执笔,再由后者认可颁布的。
关于辛亥年的和平转型,在笔者看来最有意思之处则在于,此次机遇的产生,乃是得自于精英政治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历史上常见的农民起义推动改朝换代的暴民政治模式,不容易引发大规模暴力。即使不得以而动用武力,也尚在可控范围内,故而得以顺利实现政制变革。可惜的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开头并没有维持多久,从北洋政府时期的战争频仍,到1927年以来中国政坛单极独大格局的延续,可以说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早已完全背离了前人业已达成共识的革命建国与宪政立国并行的路径,由于缺乏制衡而付出了难以历数的惨痛代价。由此看来,革命建国与宪政立国这两条路径者都自有其符合政治运作机制的合理之处,而又相互构成牵制作用,均不可偏废。
有论者认为,中国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而且在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力量基本达到了均衡状态,应当是建设宪政国家的最佳机遇,但最终没能成事,这是宿命,作者在本书里似乎也隐约持有这种观点。而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尚需到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传统不但讲求法统,而且讲求道统。但这个所谓的“道”,显然与西方社会中对王权构成实质约束的宗教力量有所区别。原因主要在于,对“道”本身拥有解释权的人,恰恰就是掌握着最高政治权力的帝王,他集法统与道统于一身。而被视为“道的守护者”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社会职能其实仅仅在于为帝王的解释权提供注释。换言之,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权力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更高的值得守护的价值,更缺乏类似于作为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的天赋人权、自然正义等超越性观念。事实上,从皇帝到官员,再到黎民百姓,除少数人外,“权利”一词是完全处于他们经验之外的东西。再者,民众从未有过参与现代政治的经验,“家天下”模式里所谓乡村“自治”,也不过是家长独裁制而已。在这种背景下,天生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暴虐,而能够制约一种暴虐的权力的,也就唯有另一种暴虐的权力而已。如此,暴力循环自然是在所难免。如果说这是“宿命”,那也许就是吧。
扯远了,再收回来。在作者眼中,《清帝逊位诏书》短短几百字却内涵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建国”与“新民”,这也恰恰是百年来我们所能想像的理想的建国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末年虽看似皇权政治的“末世”,又何尝不是开启中国现代政治之路的充满希望的年代?站在今日,回望百年,末世的挽歌因此而显得那么地凄凉,又那么地美丽。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7月版。)
- 花两三个小时草草读完此书,也就够了。
作者将辛亥革命也称为立宪时刻(P35),实在值得商榷。全书既以“立宪时刻”为题,却未认真探讨此一重要宪法概念Constitutional Moment的来源和内涵,是否算学术一大硬伤?既然作者自称随笔之作,或许可以谅解。但无论如何提升清帝逊位诏书在立宪史上的地位,除了令人赞叹状元张謇的文才了得,实在看不出其特别重大和现实的意义。
掩卷遐想,若当年清廷在风雨飘摇之际,选择与革命党人联手,又会是何种情景?——虚君共和?可惜,革命党人一心废君共和,而袁氏又得两方倚靠。哀乎,革命党人信袁氏多于当时已毫无权力和手段的清廷,终将共和成果拱手让于(毁于)袁氏。由此看来,当年之争,意气和理念大于宪政实现所亟须的妥协与退让。在这点上,当年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可能更值得赞叹。革命派未能与立宪派充分联合,又与以康有为代表的保皇派势如水火,民意无法造成统一而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持军事力量的袁氏最终得以一锤定音。 -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从制宪角度提出了有别於革命派的歴史观,指出了「被遗忘了」的立宪派进路。这种「遗忘」,可以由我们的日常国族想像中可见一斑。我们通常觉得,中国的共和建国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算起,可是,我们却忘记翌年的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其实才是民国的开端。 为甚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这就是一书的起点。
作者从中华民国制宪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种族革命传统,并不足以构成共和,立宪派的参与,以至他们与清室及袁世凯的周旋,才令中国由种族革命迅速转向共和(虽然这个共和国在事后看来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笔墨论证《清帝逊位诏书》在制宪过程中的重要性,当中涉及诸多宪法学及哲学的讨论,笔者受教不少,不敢随意点评。不过,换一个历史角度去看,高的观点并不难理解。武昌起义后,虽然引起不少省份闹自治,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即时瓦解,甚至曾派兵打击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间经历了短暂的南北对峙,议和的结果是清室决定退位下,这才没有发生广泛内战,也没有造成南北两个政权对垒的局面。
高全喜是当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在他们的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强调了立宪派士绅促成了和平的转折,他们认为,立宪士绅比之前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影响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后,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谘议局,局中的士绅多支持立宪,而非排满革命。他们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宪,组成内阁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议会,可是,清室到最后还只是推出一个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内阁,加上其他新政措施迟迟不落实,令不少士绅感到无望,因此,在武昌起义时及其后转为与革命派合作。这套历史叙事减少了对革命派的重视,只要读一读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着作,便看到这个趋势(例如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
虽然清帝逊位很大程度上由袁世凯逼宫所致,但是,负责草拟诏书的却是立宪士绅领袖之一张謇。诏书提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从一宪法高度提出「中华人民」的说法。因此,成就了中华民国宪政的,不单是「驱除鞑虏」的革命派,还有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高称之为「革命的反革命」,把革命派的种族革命转化成更阔的国族。这股改良主义力量,由晚清立宪运动辗转注入了现代中国共和宪政之中。
高教授认为,这是一份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遗产」,两个共和国共同分享却不自知的。他提出一个反问:若没有立宪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转」方式转至人民主权,为甚麼汉族革命派会承继了清朝的「汉满蒙回藏」的版图及统治权? 作者哀叹,往后的革命主义把立宪派的精神掩盖及打压了。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皆以革命为国家及国族叙事的主轴,争逐革命权威,灭杀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辞仍限制我们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起源,却不知立宪派促成的制宪时刻,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革命」。
《清帝逊位诏书》虽是划时代,却是一场失败的「光荣革命」。 国内不少知识人认为,此书虽然短小,却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历史着作之一,我是非常同意的。 - “辛亥百年”的高峰算过去了,回望一年多来出版的书籍,总体感觉是挖出了不少史料,视角多元,读来颇有收获。不过,细节的堆砌也令人迷失,观念上的迷失。历史太庞杂了,有时候故事讲得漂亮,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叙述的迷障,被纷繁的线索牵来扯去,却始终号不准脉络,无法上升到观念史的层面俯瞰和思考。
高全喜教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是个例外,他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剖析了那份即便在纪念热潮中也遭忽略的历史文献。至少于我而言,极有启发。
对于辛亥鼎革之际的清王朝,世人多以“覆灭”“瓦解”“崩溃”等词形容,是不准确的。首先,辛亥革命和屡屡重演的“王朝更替”有本质区别,它以帝制终结为起点,以立宪共和为终点,从而脱离了改朝换代的循环。这一性质,“覆灭”二字无法涵盖。其次,帝制终结也不等于国家瓦解或崩溃。辛亥后,清朝的疆域大体保存了下来,中国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努力正基于这份“帝国遗产”之上,避免了如奥斯曼帝国般分崩离析。
这两点,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均有所体现。高全喜则认为,仅诉诸此还不够,他拈出了《清帝逊位诏书》。乍一看令人迷惑:《逊位诏书》颁布于先,随即南方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两者有继承关系,按道理,“禅让”之后,《逊位诏书》的历史使命亦告终。那为什么仍要凸显其价值呢?
这得从《临时约法》的两个“短板”谈起。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立宪共和,归宿理应是“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用章太炎的话概括,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这又是一个悖论:革命既要开出宪法新法统,又要把革命自身从法统中消除,可谓“革命的反革命”,难度不小。(详见页39)果然,革命党领袖们“缺乏应有的自觉”,以致相关内容在《临时约法》中付之阙如。其实,鉴于《临时约法》由革命动力所促成,制定者有强烈的革命偏好,即使加入“反革命”条款,恐怕也靠不住。
此即“革命建国”的悖论——革命迟迟不退场,激进观念蕴于宪法中,“日常政治”无缘降临,建国之基遂难巩固。
这又引发了第二块短板,“人民制宪”的困境。任何政权的建成都需要正当性,古代政权来源于神授,现代政权则靠民意,制宪为民意的具体表现形式。辛亥革命是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一跃,跃进的目标又是“共和”,人民制宪为题中应有之义。
对此,《临时约法》制定了相应的条款,纸面上看问题解决。然而症结在于,“依照这部约法的深层宪制逻辑,其民国构建是源于国民革命”(页45),但并非清帝国的所有领土和所有民族都参与或认同“国民革命”。高全喜分析道:“满、蒙、回、藏所效忠的是清王室,其领土管辖权属于清帝国的另外一套制度,遵循的是清帝国的帝制法统,在他们看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拥护的政权只是一个南方政权……也就是说,革命党人的中华民国在法统上与他们没有瓜葛,《临时约法》对他们没有法律效力。”(页135-136)
这一层危机严复当时已看出,并深表忧虑(见《与莫理循书》)。《临时约法》的制定者也非毫无知觉,总纲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但高全喜指出,必须追溯至《逊位诏书》里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该条款才有效。简言之,《逊位诏书》“以清帝国之主人身份,稳定、安抚满蒙回藏各族之心,尤其是各族上层王爷贵族之心,以便将清帝国之全部统治权以及其法统,禅让与中华民国”。(页138)这弥补了“人民制宪”的短板,亦为《临时约法》所无法替代。
同时,《逊位诏书》体现了端方、袁世凯、张謇、梁启超等立宪派的主张,使民国建立的正当性不必完全套用激进主义的叙事,为革命退场留下出口,从而弥补了第一个短板。我认为指出这一点很有意义。从前关于立宪派的论述,如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过多强调鼎革之际立宪派偏向革命那一面,却忽视了其改良之心——遏制激进势力,将革命话语转向日常话语,从而展现出成熟的转型时期的政治智慧。
因此诚如高全喜在本书开篇中点出的,《临时约法》只代表南方革命政权所诉求的立国之宪法,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尤其是北方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政治决断。必须加上《逊位诏书》,两者构成“一组宪法性法律”,方才是“作为民国肇事之立国根基的根本法”(页10)。这也是高教授视《逊位诏书》的颁布为“中国版光荣革命”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证伪了那种把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说成是源自孙中山“私相授受”的观点,也抽掉了南方临时政权于议和成功后将政体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的法理依据,而沦为彻底的政治伎俩。
然而,“中国版光荣革命”还是毁于层出不穷的政治伎俩。党争、政争勾心斗角,复辟、革命轮番登场,中国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思潮推入沼泽,宪政等现代价值也因丑陋的现实被“证明”不适于国情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终,革命话语胜出,革命占领宪法,改良销声匿迹。这,就不是宪法学能解释的了。最后我想提醒,以高全喜教授未在“考据”上下太大工夫而斥《立宪时刻》为“沙上建塔”的,实乃肤浅之论,他们未能洞悉这样的道理: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
- [《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1期,责任编辑:刘昕亭]
高全喜教授新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所揭示的主题无疑甚有震撼性。但是,读完全书,我很沮丧地发现,该书堪称为研究失败的例子,其致命之处在于将眩目的“高论”建立在错误的史实基础上,并由此作了过度的引申,有些地方近乎“无中生有”。该书作者无视史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将一份历史文献与事件发生前后与之密切相关的史实割裂开来,试图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掩盖其论据之不足,美其名曰“更为重大的历史真实”。该书唯一尚可称道之处,在于指出《逊位诏书》对满蒙回藏人民及边疆土地顺利归入中华民国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这也只是一篇论文的题目,不必大肆铺张,推衍成十几万字的专著。
学术上种种不审慎
该书一开头就将作者不谨慎一面暴露无遗。“袁世凯洪宪帝制破灭后,中华民国的宪法创制重新开始,历经十年,1923年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该书第1-2页)。袁世凯死于1916年,“历经十年”怎么会才到1923年?
“缺乏一部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现代宪法,这确实是一个遗憾,也正因为此,第一共和国的历史才充满了政治暴乱、军事内战、军阀割据和独裁专制”(本书第6页)。用“第一共和国”这种外国史概念硬套中国史,殊无必要。据该书注释,“第一共和国”指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如此,直接用“中华民国”岂不是更为明确、绝不会引起误会?这还只是细枝末节,关键是这句话所下的判断,换言之即是:假如有了一部所谓“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宪法,民国时期的种种政治弊端皆可避免。要下这样的结论,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论证,而不能当作人所共知的“自明的公理”。姑不论当时有无从容制宪的环境,这里面实际隐含着对已发生的历史作假设,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已发生的史实不能再改变,对此作种种“假如……会如何”的假设,或许是一部穿越小说的题材,却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
作者在回顾晚清变法时,指出“康梁倡导的戊戌变法……乃是借鉴西方现代国家的宪法或塑造宪制国家的根本法”,并引了康有为的所谓“上书”:“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第28页)。看起来在1898年康有为已经正式向光绪皇帝提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制”的建议,可谓先知先觉。但是,且慢!这一段引文的出处,据作者注,来自麦仲华编《康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宣统三年刊本第32-34页)。这本《戊戌奏稿》所收录的奏折,经过黄彰建、孔祥吉等学者多年的严密考订,早已证明是康有为后来改窜的版本,根本不是戊戌的原本。而这一段话所属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据黄彰建考证,恰恰是到了1905与革命派论战时新写的,“用以应付革命党人的攻击。”(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3月,第689页)高教授若查阅一下黄彰建、孔祥吉的相关著作,或者查对黄明同、吴熙钊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的《杰士上书汇录》,就会发现,戊戌年康有为根本就没有上过这么一份奏折!
接下来,作者又将武断的作风重演一遍:“派遣冯国璋领兵讨伐,冯系袁世凯手下将领,此次南下用兵自然是了无战功”(第71页)。事实是冯国璋此次用兵战功卓著。10月29日冯氏接任第一军总统,11月2日即攻克了汉口,11月27日攻陷汉阳,令湖北军政府被动万分,已有人提议撤出武昌。还是袁世凯出于利用民军势力压清廷屈服的考虑,电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后来又将指挥权移交段祺瑞,才让武昌转危为安。
作者指出:“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第115页)。我们在书中只看到对冯玉祥逼宫的单方面指责,好像溥仪小朝廷完全无辜,只是冯玉祥“违约”,却全然不顾此前张勋复辟时,溥仪先已违反了逊位诏书的约定,即民国优待清室是以清室及时退位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前提的,既然清室复辟帝制,即是公然违约;再进一步来说,条例规定清室必须移居颐和园,故宫只是“暂居”。我们可以指责冯玉祥在处理方式上过于粗鲁、不近人情,但从法理上来说,这是溥仪小朝廷率先违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逊位诏书》原稿代表革命派立场
在第三章,作者将历史学界对清帝退位时期袁世凯“精于弄权”、隆裕太后“勉强而被迫地同意退位”这样公认的结论称为“时下众多论者的轻薄之见”,认为是“一层表面现象”,并且指出“至于诏书是由何人代为拟写,清帝和太后处于何种情势下的迫不得已、理智懵懂,等等,其实已经不甚重要了,我们岂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且不论将史学界的共识认定为“轻薄之见”极其无礼,作者脱离历史文本的具体语境,把它孤立出来加以拔高,再作无限度的引申发挥,已构成本书最重大的缺陷。
《逊位诏书》原稿由张謇所起草,这是史学界的共识。能否说诏书原稿代表着立宪派的立场呢?不错,张謇曾经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但高全喜显然对于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迅速倒向革命的史实缺乏了解。据《张謇日记》记载,1911年12月2日,得知南京光复,张謇即到上海与革命党骨干章士钊、宋教仁、黄兴、于右任会面,10日剪掉辫子,16日到南京,19日受命担任革命政府的盐务总理,20日动员商会给革命军筹20万军饷,1912年1月2日“被推为实业部总长”。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起草逊位诏书的时候,张謇已经是革命政府中的重要一员。
逊位诏书原稿,不仅是张謇担任南方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期间所起草,还经过革命领袖孙中山、胡汉民审核通过,完全代表南方临时政府立场。该稿用电报方式发到北京以后,袁世凯幕僚按照袁的授意,擅自修改、添加了内容,其中有一段“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即是袁氏偷偷添加的“私货”(参考刘厚生《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回忆》);袁氏巧妙利用了退位诏书发布后不便修改的人之常情,制造从清廷取得“授权”的假象,以挟制南方临时政府。孙中山此前早有预料,于1月20日告知议和代表伍廷芳“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并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2月13日)致电袁世凯:“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无穷枝节。”(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6页)孙中山这个电报构成了对袁世凯单方面修改《逊位诏书》行为的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授权,来自代表全国多数的南京临时参议院(17省代表一致通过,已达到合法的多数)。
无论作者如何拔高,都无法否认这么一个事实:隆裕太后是出于保住清室优待条件的考虑,被迫颁布诏书的。诏书原稿早已由议和代表伍廷芳拍发给袁世凯,清廷一直拖延发布,直到伍廷芳通知袁世凯“若2月11日上午8时停战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则所订优待条件作废”(《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38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5页),隆裕太后无奈之下,才同意发布退位诏书。
作者不惜贬低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抬高《逊位诏书》的作用,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觉,以为诏书代表了所谓“立宪派”的立场,不了解张謇虽然此前被目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此时已经完全投入到革命阵营。张謇的起草行为,得自临时政府领袖的授权并经过其审核,只能代表革命派的立场。可以说,《临时约法》和《逊位诏书》原稿,都是临时政府所制定的,构成了所谓“宪法文件”的一个整体。如果说诏书有着如何深远的宪法意义,也是革命党所主张的。抬高一个,贬低一个,毫无意义。
北京大学李启成副教授在《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一书前言中,曾感慨地说:“短短百余年间,正式颁布的宪法、宪法性文件,可谓洋洋大观。就这些众多宪法文本的内容考察,其质量之高,比之发达国家的成文宪法,毫不逊色。”李启成虽对各种旧宪法未能真正实施以致成为“遮羞布”深致不满,但仍肯定这些宪法或宪法草案的文本质量。所以,尽管临时约法在权力划分上有一定问题,关键仍不在宪法、宪草的文本自身,而在于应该遵守宪法的各方人士并不从心底里尊重宪法。
过度引申与自我重复
逊位诏书得以颁布,是革命党和袁世凯集团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袁世凯的私自修改在法律上缺乏效力,已被孙中山致伍廷芳、袁世凯的电文所否定。诏书中除了宣布退位一事(这个是迟早的事),比较有价值的是“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陈述,连同优待满蒙回藏的附加条款,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从效忠于满洲皇室过渡到效忠于中华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华民国得以顺利继承清帝国的全部人民和土地。张謇起草诏书的时候,无论是出于自身原有的大局观,还是受了孙中山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转变的影响,其原稿文本最终都经过临时政府领导层的同意。高全喜在本书中对此一陈述的意义加以揭示,有一定贡献,但也只是揭示而已,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2010年5月12日,高全喜曾在人民大学做过题为《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的演讲,提出“作为研究宪法学的学者,假如一生把宪法学作为一个事业的话,我觉得需要三种品格:一种是坚毅,第二种是审慎,第三种是节制”(见“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从这本新书来看,“审慎”和“节制”可以说是不见踪影。作者之“不审慎”,我在前面已经充分加以揭示;而作者之“无节制”,则体现在将简单的观点,用不同的语句组合,反复陈说,推衍引申,看起来字数很多,其实“干货”就那么几条,条理既不清晰,焦点也变得模糊。
高全喜此书入选一些新书榜单,作者又在全国巡回演讲,博得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好评。这篇批评文字,势必让一些朋友不快,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在学术上不谨慎的人,你能否相信他能始终忠于崇高的理念?任何高尚的愿望,需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近代中国有太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例子,结果“正义”的事业被卑劣的手段所毒化。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著作去推广某些或许高尚的理念,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不要也罢。
- 反对高某观点的无非是这么一种观点,也就是清帝逊位诏书是清帝无奈的举动,其实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以下两点
一清帝逊位诏书代表的不单是清帝的意志,也代表着北洋派和立宪派的强大意志。是他们的联合阻击阻止了以孙文为首的极端激进派的破坏趋势,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和中国的分裂
国民党篡改的历史,为了造就自己的所谓正统,把袁世凯的继位说成了继孙文南京临时政府之位,这样就可以使得国民党伪造历史,把孙文篡改成所谓民国之父。然南北统一曾经有一个月的分立政府时期,清帝宣布退位,造就北京临时共和政府。南部各省宣布独立,成立南京临时共和政府。南北政府会谈,在造就统一的中华民国共和政府。袁世凯之权力并非来源于国党所鼓吹的孙文,而恰恰是在清帝退位后权力转移授权给北京临时共和政府和南方进行创建民国的谈判,后来袁和南方政治妥协最终建立统一的民国,这一历史事实长期被国民党所篡改
袁是真正的民国之父,而孙文的南京临时大总统,非但国际不予承认,事实上内部后来也不认同孙文。就是所谓的临时约法,也是孙文违背法统通过的烂污东西(临时约法通过按组织法需要三分之二议员出席,是时武汉和浙江同孙文分裂,两部议员返回,人员只有一半,且都是同盟会会员)
二,诏书肯定了民国对清代疆土主权的继承,维护了国家统一。大家都直到,以孙文为首的极端激进主义货色和现在的光头党一样,是根本不知道国家认同是何物的,早在1902年梁任公提出中华民族说,凡认同中国者即为中国人,而孙文之辈却去祭祀本族暴君朱元璋,在他眼里,中国就是本土十八州,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是本族奴隶主当政就行。所以才干出一再把东北和边疆地区作为夺权筹码让予日本和俄国的蠢事,因为他是个没有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观念的人,他的国就是他统治下的乌托邦,非他统治的中国他都要反都可卖。在极端激进主义的宣传下,当时的反满主义非常厉害,革命党自己伪造成满人,发布所谓的灭汉种策,宣布满族人要尽屠汉人,在这种妖魔化宣传下,辛亥革命中极端派也发生了众多的屠杀旗人事件,比如广州西安的人头井之类。在这种极端主义宣传下,边疆地区离心非常严重。肃亲王等提出劫持末帝出逃东北,依靠日本建立东北政权。蒙古贵族分成两派,一派忠于清朝,一派予以依靠俄国独立。西藏达赖试图驱汉。如果顺孙文之流极端激进派观点,中国必将分裂,且德国纳粹的水晶之夜会提早多年在中国上演,然北洋和立宪派及清室合力而达成的退位诏书,以国家形式把清代疆土等继承于民国。蒙古亲清朝势力平定了亲俄势力的叛乱,追随清帝归顺民国。西藏达赖失去了独立之理由,肃亲王的计划也彻底破产
为了篡改伪造历史,为了塑造国民党所谓的正统,拼命塑造孙文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以至长期抹杀北洋派,立宪派和清朝在辛亥中所起的作用和。事实上孙文被立为正统,乃1927以后两党塑造的正统历史观的结果。国党以形象物化(中山陵的建造),主义独尊(三民主义的奴化宣传),符号圣化(总理遗教,奉安大典),仪式推展(总理纪念周)等方式伪造历史,重塑孙文形象,非但把立宪派和北洋派,清帝在民国建立中的功劳全部一笔抹杀。甚至把不同孙派的光复会,杨衢云,黄兴,宋教仁等的历史全部篡改抹杀。1940年4月1日,国党常委会第143次会议正式训令,册封孙文为中华民国国父,这种国父如此而已
- 辛亥百年,学界再次掀起研究辛亥革命的热潮。这一次,焦点不仅仅凝聚在革命党身上,作为革命对象的清室以及作为第三方出现的立宪派不再只是革命党身边的陪衬,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的研究范围。回首百年,历史学再一次拓宽了它的视野,让我们能够更加完整、更加全景也更加深刻地理解辛亥百年。
即使在这一背景下,《清帝逊位诏书》仍然是个冷门,不过是为清室下台争一个体面而已,似乎没有什么研究的余地。然而,高教授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清帝逊位诏书》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退运文件,而是与《临时约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开国的宪法性文件,其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临时约法》。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高教授引经据典,在开篇还特意详述了一番革命成功后的立宪时刻并将此作为书名引起读者的重视。在高教授看来,辛亥革命后这个关键的立宪时刻,《临时约法》有着严重的短板,需要《清帝逊位诏书》来加以修补,甚至后者才是民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如此厚爱,当年起草诏书的张謇老先生要是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实在是诏书不可承受之重。
辛亥年,中国在政治力量无非可分四大类:清室、革命党、立宪派、北洋军。正如诏书所言,武昌起义之后,九夏沸腾,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南方各省先后宣布独立,革命已成燎原之势。面对革命党的咄咄逼人,清室能否再像当年太平天国时那样渡过危机,关键在于北洋军的态度。南方革命虽然初现燎原之势,但当时革命党要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推翻清室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政治上讲,在南方各省独立的过程中,革命党固然是重要角色,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自感被清室预备立宪所蒙骗的立宪派,他们本来就属于两头飘摇的中间派。如果清室真心实意地推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是会死心塌地地拥护清室,正是由于清室推行假立宪,立宪派才倒向民国,但是武力革命始终不是他们的主张,一有南北议和的机会绝对不会放过。从军事上讲,革命军几乎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从同盟会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就可见一斑。武昌起义后,面对北洋军的攻势,革命军并无佳绩。如果北洋军全力进攻,不要说武昌,南京恐怕都难以保全。
因此,面对虚弱的清室、飘摇的立宪派、外强中干的革命党,中国的前途取决于北洋军,取决于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素有野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于是运用两面手段上下其手,顺利窃得这个偌大的中国。面对革命党武力的孱弱和急于求成的心理,袁世凯给了清帝退位的大果子。面对无助的清室,袁世凯像模像样地争取来优待条例。面对飘摇的立宪派,袁世凯以自己的实力许以民主共和的美好蓝图。因此,清帝退位绝非自愿,而是袁世凯威逼利诱的结果,《清帝逊位诏书》不过只是一份体面的下台文件而已,仓皇下台之时哪有闲情逸致规划这个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所谓的宪法精神恐怕是起草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在这里,不是起草者想少了,而是高教授想多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习惯于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百年来,由于危机的深重和紧迫,中国革命多采用激进手段,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高教授被激进革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所苦,憧憬和平建国、民主立宪的美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学者的观点,但凡在国家危机深重且紧迫之时往往趋向武力激进,而当社会安逸之时则寄情于和平改良。时下虽存在诸多问题,在从历史上看仍不失为太平之世,学界观点倾向改良也属正常,但要是将自己的政治好恶强加给古人,甚至附会在被逼迫出来的《清帝逊位诏书》上恐怕就不太适宜了。诏书中即使有一些与立宪思想相合的语句,恐怕也是张謇这个老立宪派“以公谋私”的产物。
除了自己的政治好恶之外,高教授还在清室的脸上扑粉,添加了太多一厢情愿的想象,仿佛清室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千古圣君。高教授认为,根据诏书的内容,清室已经认可了革命的正当性。可是,这个前一刻还在抓捕、镇压革命党的统治者怎么可能在瞬息间幡然醒悟?对于共和政体,诏书中固然有“南中各省倡议于前”,但更重要的是“北方诸将主张于后”,失去统治支柱的清室为保全优待条件被迫选择退位。自从周公天才地发明了天命说之后,与历朝历代的末代帝王退位一样,清室退运也需要找来天命人心作为遮羞布,装出一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的圣人模样来。更有甚者,高教授认为清室退位是为了避免百姓陷于战火的大义之举,更是不知从何谈起。如果清室如此伟大,当年洪秀全振臂一挥,咸丰帝就可以逊位了,何以打得江南涂炭?从连立宪派都伤透了心的预备立宪骗局来看,清室从来就没有立宪共和的诚意,万般无奈之下才搞出一个《十九信条》。无论从理论上讲《十九信条》多么先进,对于一个信用全无的王朝来说,只是一纸空文,作为下台文件的《清帝逊位诏书》也不可能带有多少立宪共和的诚意,日后的张勋复辟更是证明清室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立宪共和。为了证明诏书的宪法性,高教授还搬出了社会契约论。可是,优待条件哪里是什么社会契约,不过只是袁世凯诱使清室退运的交易条件而已,连革命党在北洋军面前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何来社会契约之说?后来,张勋闹复辟,清室积极参与,失败之后与北洋政府的合同终止也属咎由自取。
在高教授看来,清室的精神是崇高的,逊位本身自然也就成为所谓的“光荣革命”,只不过毁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和激进革命的闹腾。殊不知,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在于深厚的社会基础,一个尚未进行大规模民主启蒙的古老国度何来光荣革命的基础?北洋军阀这些脱胎于专制王朝的旧官僚显然靠不住,缺乏经过民主启蒙的广大民众的动员,纵然宪法文本再完善也无以自行。激进革命的负面作用虽然显著,但对于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说,也只有激进革命的煽动性才能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启蒙动员,为民主共和的实现奠定基础,任何对于统治者的光荣革命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武昌首义,南京临时政府开创了民国,近代中国的长期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高教授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只代表南方,南北和议之后组建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因为南京临时政府没有清帝授权,更没有外国承认。然而,革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革命对象无异于与虎谋皮。同时,作为一国内政,革命政府的合法性也不需要来自于外国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没有国民政府的授权,也没有多少外国政府的承认,难道就因此而丧失了合法性吗?高教授的推理来自于法学理论,但法学理论来自于生活,但绝不能强奸生活。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因其革命性而生,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及其内阁都是经过南京参议院的同意才取得合法性,袁世凯也多次声明遵守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作为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南北和议后组建的北京政府只能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延续而不能否定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回首辛亥百年,学界的研究日渐全面和深入,纵然是翻案史学盛行的今天,我们更应当从历史的深厚基础出发,更加全面地认清历史,看清现在,而不是用现代的主观臆想去强解历史,给历史负上其不可承受之重。 - 所谓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国家创制,皆表明它是由各种制宪力量氤氲汇合而形成的。
清帝放弃国家权力于国民,而获得民国清室优待条件之认可。而袁世凯则通过南北谈判结果获得中国民国国父的实际,真正的民国之父是袁世凯,而不是孙文,孙文只是代表南方的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是代表全国范围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并获得参议院确认,从法统上讲,清帝交于权力与国民,南北组织谈判建立民国政府,袁世凯作为南北双方合议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被称为中国的民国之父当之无愧,但也因此被套上了共和的紧箍咒,导致了其君宪称帝的合法性丧失
事实上当年孙文以能获取国外承认和提供外力经济援助的欺骗前提下,在武汉集团和浙江集团权力争夺相持不下的前提下,所以折衷选出孙文作为他们政治妥协的暂时代理,本就是虚位以待.谁料孙文在一系列的对日卖国未成.签定满洲租借协议谈判不成后,外国承认和经济援助一无所有,遂武汉集团和浙江集团对他反目,内部弹尽粮绝,四分五裂,孙文武力统一政策无能为力,才被迫对袁妥协,这个位置不是孙文让出来的,而是袁是当时南北乃至全国能够共同接受的人物所致.国党所喋喋不休的所谓孙让袁继,只不过是国民党自编自导的政治谎言而已
事实上,孙文在清末时期,就建立了自己训政的设想,如果孙文在1911年有实力夺取政权,则中华党国般的把人民当猪狗来训的独裁政体会提早上演,孙文的训政设想不是什么共和失败后形成,而是在同盟会里就已形成,由于民初共和的失败,袁世凯大总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君主宪政上,而孙文则把训政设想建立在学习苏俄的党国体制之上
激进主义最终葬送了改良的机会和希望
- 中国版“光荣革命”的意义
——读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
杨津涛
刊于8月8日《人民政协报》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宣统帝奉隆裕太后懿旨,颁布逊位诏书。这在结束了清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同时,也宣告帝制从此退出中国历史。此前的所谓南北和谈,其实只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谈判,清室作为最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反而变成局外人,命运操在了他人之手。当优待条件谈妥,清室也唯有交权一途了。以政治史叙述来说,这种诠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以政治学视角,重新看待清帝逊位,那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新统治者都特别看重对旧王朝“正统性”的继承。但是清帝退位,民国肇始,既不是权臣篡位,也不是造反起事,那么如何使新生的共和国从旧王朝那里“合法”地继承权力呢?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南方革命党人发起,此后虽有立宪派士绅参与其中,但是创建民国的主导者无疑还是革命党人。逊位诏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它使得推行“预备立宪”多年的清廷参与到了第一共和的建立中来。改良与革命两条立宪路径,在这里得以殊途同归。因为宪法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而《清帝逊位诏书》事实上参与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所以使其具有了宪法的意义。所谓“正统性”从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在《立宪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所探讨的《清帝逊位诏书》,除《逊位诏书》外,还包括同日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在高全喜看来,这一揽子文件绝不仅仅是袁世凯为获得总统之位,而迫使清室交出政权的一纸文书,更是一份南北“双方都接受并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清帝肯于让渡权力,那是因为即将建立的统一新政权,不再是世袭王朝,而是人民主权的共和国。正是基于南方创建共和的承诺,以及三项优待条件的交换,才会有上述的《清帝逊位诏书》。既然逊位诏书具有契约性质,那双方就必须同时遵守,所以无论是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还是前清的废帝溥仪,一旦复辟帝制,也就背弃了诏书精神。
在作者看来,清帝以和平方式退位,同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堪称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它使得革命建国的激进主义内容大为削减。恰如几天后,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那样,“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谈及逊位诏书,那就不能不说说袁世凯对其“篡改”的故事。依据新近披露的《赵凤昌藏札》显示,近年所见的逊位诏书是由赵凤昌策划、洪述祖拟出初稿、张謇拟出二稿、最后呈交袁世凯审阅的。作为政治学学者的高全喜不太确定,那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话究竟是否真的为袁世凯所加,其实在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中即收有袁世凯对逊位诏书的修改稿。如作者所说,这一改动在宪政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逊位诏书中的“袁世凯条款”,将“帝制法统转化为共和国的法统”,既以类似禅让的形式,将统治权移交给了袁世凯,同时又给他加了一道紧箍咒——给你权力,那是叫你创建共和,而不是开辟新朝。
在本书正文之外的大量注释中,作者以政治学学理与古今史事为鉴,指出在革命后的“立宪时刻”,《清帝逊位诏书》保留了皇室的尊荣,对上继承了古老的传统文明;此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又向下开启了现代政治。一份隐含深意的历史文件,由作者的精心阐释,得以被重新认识。
http://epaper.rmzxb.com.cn/2011/20110808/t20110808_405672.htm
- ……不囿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单纯从现成的规范主义出发,而从现代政治的发生学来解读和审视中华民国之宪法,力求在众多或明或暗的历史资料中,挖掘那个活的民国之宪法,洞开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源。
在当今的语境下,我们要和平地致力于国家建设,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源头,去发现第一共和国的“立宪时刻”,发现这个非常时期的真实“宪法”以及宪法精神。
从政治宪法学的更为高远的视角来审视《临时约法》与《逊位诏书》所分别代表的两种立宪建国逻辑之间的的张力,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中华民国的制宪史,理解中华民国作为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立宪时刻”所蕴含的渊深的宪法内涵,理解我们今天的制宪建国事业,不过是中华民国在肇始之际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的继续。
从中华人民的国家构建来说,《逊位诏书》是对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清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即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即“共和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
我认为中华民国之构建,是两种具有现代性的革命之折冲、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它们都超越了汤武革命的传统革命含义,而具有现代共和立宪与民主制宪的正当性理据,从历史大尺度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两种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革命史观都是片面的,现代革命的实质不在于要多么彻底,而在于是否付诸于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这才是一个现代国家之构建的核心原则。
本书的全部分析,其宗旨就是要指出《清帝逊位诏书》所包含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宪法精神,将其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以“革命的反革命”契约折冲或消弭了革命激进主义的片面性,由此,《清帝逊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之根基。
任何帝制复辟都是违约的倒退,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而且也是对逊位君主的背叛。但文化、文明以及煌煌千年中华之灿烂典章礼仪、道德文学等等,却完全可以为中华民国富有生命地传承,甚至还可以主动而有意识地凝聚于中华人民对逊位王室的光荣尊崇之中。实际上,逊位诏书中的清帝和王室优待条件,已经明确规定了上述内容,并且具有着宪法性的意义。但是,两次复辟却将这个原本在共和国之政治基础上的具有着伟大前景的传统文化事业彻底毁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最后,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而且也斩断了中华民国与传统帝制之间曾经通过逊位诏书所发生的契约性联系,斩断了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最后脐带,把这个王室所可能维系的传统文明之尊仪和光荣一起彻底消灭了。
历史不堪回首,对于上述三次涉及逊位诏书的重大事件(张勋复辟、驱逐清帝离开故宫和日本人建立满洲国),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予以应对,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关乎一个现代的中华民国之人事与天命问题。本文试图从逊位诏书中发现和挖掘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制宪建国之精神,并且揭示蕴含其中的由两种力量所熔铸的“革命之反革命”的宪法精神,无非是为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有所警示。
这里涉及中国三千年古今之大布局中的一个不期而然的宪制塑造问题,或许可以说,这里本来隐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个百年未有之机遇擦肩而过,不再复返。
清帝逊位诏书之拟制的准虚君共和制设置,本来对于一个政治成熟的现代共和国来说,是完全可以大做文章,把其蕴含的文明传承和古典精神与现代人民主权以及宪制架构巧妙地融汇于一炉,开出中华民国之古今传承之新法统的。然而,这个机会被后来者历史性地错过了。由此,彻底打倒了旧制度,全面祛除了旧法统,现代中国如何接续传统,现代政治如何凝聚人心,现代法制如何被人尊崇,人民如何能够不腐化堕落,国家如何能够被人民信奉,这一切就都将成为现代政治的攸关问题,直到目前尚未彻底解决。
在南北和议、《清帝逊位诏书》颁布之前,清帝国之疆域大有分崩离析的解体之势。正是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他们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这个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之完整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份诏书宣示的那些原则,蕴含着非常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尤其是其中隐含着的有关革命、中华、人民、立宪、共和等关涉一个现代共和国之生死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是对于晚近以来狭隘的革命建国的政治路线与衰颓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新形式的整合与升华。
-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证伪了那种把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说成是源自孙中山“私相授受”的观点,也抽掉了南方临时政权于议和成功后将政体从内阁制变为总统制的法理依据,而沦为彻底的政治伎俩。
——————————
这个角度指的是“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尤其是北方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政治决断。”,言下之意,加上《逊位诏书》,两者一起才能代表。反推也就是说:《逊位诏书》补上了《临时约法》不能代表的北方民众的代表权。
OMG!抱老师自己说“古代政权来源于神授”了。那它只能把自己有的“神权”部分拿来“让渡”,不能把自己没有的部分“民意”拿来送人吧? - 这个是转型问题,关键看“被代表的民意”认不认,认了就有正当性,再去追问“合法性”就是不必要滴。当然,所以说,逊位诏书加强了认的权威性和可能性。
- 补充下,政权的正当性问题就是大家认不认的问题,转型时期这个最重要,合法性倒未必那么重要,相反可能还有害。
- 啊,我没说临时政府的总统制没有合法性啊,我是说加上逊位诏书的法统后,民国的法统才完整;而因此,在逊位诏书颁布后临时政府又“将政体从内阁制变为总统制”,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 丫,没注意,居然写反了,应该是“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好笑话了。
逊位诏书颁布前南方政权决意采总统制,逊位诏书为袁世凯所促成,其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清帝逊位后他任总统。谁知诏书颁布后却因孙大炮做不了总统而要改成内阁制,岂非纯粹的政治伎俩?这是破坏双方默认的政治规则的行为。自然无正当性。 -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惭愧。我本应该理解你的原意的。我把前面两条误会的留言删除了,请抱老师见谅。
- 讨论“证伪了那种把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说成是源自孙中山“私相授受”的观点”必须搞清楚大总统职位“私授”的反面是什么?是否应该是大总统职位“公推”?
如果是公推,在正式的选举前,候选人的得胜是一个不可能确定的问题。即使如华盛顿总统,当年选举时,据说汉密尔顿还为了怕亚当斯胜出做了些当时人看来不怎么光彩的拉票呢。
如果如此,那么袁世凯确实是私授得到的大位,他一方面得到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的私授,一方面得到清室的私授,逊位诏书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在此后的总统选举时,已经绝无袁不当选的可能了。
所以最多说,袁的大位不是仅仅来自孙的私授罢了。
至于说“也抽掉了南方临时政权于议和成功后将政体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的法理依据,而沦为彻底的政治伎俩。”
此举是政治伎俩不错,但是不是没有法理依据,还值得商榷。即使认为退位诏书构成宪法性文本,诏书也只是说:“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既然只是协商统一办法,也就没有规定死袁世凯是zhmg实权总统。按照临时约法,“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与诏书“全权组织”并无明显相悖之处啊?只能说gm政府有些人太下作。 - 是我写错的,错在我。
关于法律依据,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仍然认为,既然把逊位诏书视作宪法性法律,而其背后已有双方就认可的“默识”,则事后改为内阁制,至少构成对诏书的阳奉阴违,是违背其本意的。而这个本意,原本就是是南北议和的结果。 - 虽然还没读过,但总感觉若如此,颇有康有为两考的企图。。。
- 呵呵,自己都不严谨,还敢笑别人吗?
是黄彰健,不是黄彰建,OK? - “缺乏一部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现代宪法,这确实是一个遗憾,也正因为此,第一共和国的历史才充满了政治暴乱、军事内战、军阀割据和独裁专制”(本书第6页)。
换言之即是:假如有了一部所谓“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宪法,民国时期的种种政治弊端皆可避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觉推导不出来啊。似乎不合逻辑吧? - 假如有了一部所谓“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宪法,民国时期的种种政治弊端皆可避免。要下这样的结论,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论证,而不能当作人所共知的“自明的公理”。
確乎如此。至少英國憲法並非人民制憲權產物。
对已发生的历史作假设,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已发生的史实不能再改变,对此作种种“假如……会如何”的假设,或许是一部穿越小说的题材,却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
以上規範不存在,至少英國史學大家無此成例。霍布斯鮑姆、泰勒非但運用假設,而且用於全書立論核心部分。
票友想象規範,往往失之誇張。學術規範不過約定俗成之習慣,並非一成不變。剛性條款(例如不得超過N千或萬字之例)一般出自外行,大多有害,後人視之不過八股格式一類。 - 《逊位诏书》原稿代表革命派立场
此節完全運用訟師技術,偷換概念:
所引證據證明:
《逊位诏书》原稿代表南京政府立場,
然而,
南京政府並不代表革命派立場。
相反,
革命派迅速邊緣化,為士紳-立憲派所制,迄今一向為史學界主流意見。 - 作者指出:“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既然清室复辟帝制,即是公然违约;再进一步来说,条例规定清室必须移居颐和园,故宫只是“暂居”。
不可誤會“憲法主體”概念----產生憲法,而非憲法所產生。憲法程序(軍事政變其實不在程序內)不能廢除先於憲法而存在之憲法主體。例如:塞爾維亞國會無權廢除南斯拉夫其餘聯邦主體之主體地位。有之,憲法危機已經不可能在憲法框架內解決,必須付諸內戰仲裁。
解釋條約或憲法無法達成一致,本身即為戰爭理由,適用於國際法慣例“交戰國與交戰集團”規範。戰爭即為仲裁,而非以某種抽象主義或“誰先動手誰没理”仲裁。“誰先動手誰没理”已經屬於“解釋條約或憲法無法達成一致”,構成戰爭理由。 - 2010年5月12日,高全喜曾在人民大学做过题为《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的演讲,提出“作为研究宪法学的学者,假如一生把宪法学作为一个事业的话,我觉得需要三种品格:一种是坚毅,第二种是审慎,第三种是节制”(见“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从这本新书来看,“审慎”和“节制”可以说是不见踪影。
制憲者之
“审慎”和“节制”
絕不等於史家之
“审慎”和“节制”
原書並非正確,然評論者錯誤已多。 - 第一,“指出《逊位诏书》对满蒙回藏人民及边疆土地顺利归入中华民国所起的积极作用”,绝非仅仅“尚可”称道,而是长期被忽视的大关节。
第二,“键是这句话所下的判断,换言之即是:假如有了一部所谓‘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宪法,民国时期的种种政治弊端皆可避免。”高全喜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是作者自己没读懂吧。
第三,冯玉祥驱赶溥仪的“正义性”源自清帝复辟,这段更属荒谬。高全喜明明说了,复辟是违背诏书的,冯玉祥所作所为也是违背的,并不因为前者错,后者就对了。并且,清帝复辟之前先有袁世凯复辟,要论,也是共和违背在先。
有此三大错,此文何足论。不过是为孙大炮张目、为“革命”正名的三流文章罢了。 - 高全喜此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宪法理论为“人民主权论”,以此观照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的得失。但本文作者显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被革命叙事迷障了。
- 作者指出:“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第115页)。我们在书中只看到对冯玉祥逼宫的单方面指责,好像溥仪小朝廷完全无辜,只是冯玉祥“违约”,却全然不顾此前张勋复辟时,溥仪先已违反了逊位诏书的约定,即民国优待清室是以清室及时退位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前提的,既然清室复辟帝制,即是公然违约;再进一步来说,条例规定清室必须移居颐和园,故宫只是“暂居”。
不可誤會“xianfa主體”概念----產生xianfa,而非xianfa所產生。xianfa程序(軍事政變其實不在程序內)不能廢除先於xianfa而存在之xianfa主體。例如:塞爾維亞國會無權廢除南斯拉夫其餘聯邦主體之主體地位。有之,xianfa危機已經不可能在xianfa框架內解決,必須付諸內戰仲裁。
解釋條約或xianfa無法達成一致,本身即為戰爭理由,適用於國際法慣例“交戰國與交戰集團”規範。戰爭即為仲裁,而非以某種抽象主義或“誰先動手誰没理”仲裁。“誰先動手誰没理”已經屬於“解釋條約或xianfa無法達成一致”,構成戰爭理由。 - 诶,心平气和的评嘛。作者反复的强调,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所以你们不在一个层面谈问题,或者你们侧重点不一样。不要专找小细节批,多考虑这种观点所有的建设性作用,即使是建在沙上的。
- 业有侧重,各抒己见,作者何必刻意压低高先生,仿佛自己洞若观火似的。高先生的研究成果学界自有公论,此书本就不是严格的学术作品,高先生兴之所至意之所发,一点见面的剖析在宪法学上的理解,门外汉岂能尽得其旨?作者何苦挖石自填,徒增茶时谈资云云。
- 此评论显然是外行,细枝末节,吹毛求疵,由此也可见其宪法学知识之匮乏。
- 唉,看出此评论的短和小来。
感谢,数卷残编。
感谢,刀劈三观。 - 历史,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付之一笑即可。 - 顺便说一句,所谓的优待清室条件通过本就说明以孙文为首的激进派在当时没有势力,如果按照孙文的思维,那么民国时期孙殿英的挖皇陵被国民政府不了了之,刺杀孙传芳的凶犯被无罪释放的事情早就发生,清朝皇族甚至旗人被全盘屠灭的事情亦有可能发生,这也正论证了高某论点的有力性,也就是退位诏书是北洋,立宪和清室对激进势力的有力歇制,直到1927年所谓的国民革命成功才无力挟制
又论及所谓清室优待条件之背叛,高某也举了三个事情,一张勋复辟违背了优待条款,然康有为,张勋等则以清室退位是以交付于国人建立民国共和,民国首先背叛搞起帝制,弄得乌烟瘴气,是为民国毁约在线。其次段祺瑞再创共和后,并为追究末帝责任,事实上继续保持优待条款。然第二次冯玉祥逼宫何能代表民国?冯某为北洋叛将,又非当时合法政府首脑,其何以代民国来毁约?所以以清室复辟在先,所以冯某逼宫有理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以南京为首都,正是表明其以集成孙文正统为继承,继承的是南京临时总统,而视北洋议会政治为伪朝,此民国非前民国,冯某背叛北洋后叛投党军,视为逼宫行为为国民党认同为正确,而在末帝看来自为民国背约,乃有挖皇陵而国民政府之不顾,遂有后伪满成立之事实 - 孙文直到解职前还在向日本叫卖利权,一旦达成交易,就不跟袁罗嗦了,直接挥师北伐。幸亏孙文卖国未成,否则大东亚共荣圈早三十年就出现了。
- 大炮啊大炮,还铁拳无敌呢,哈哈
- 正因为大炮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暗合之处,三十年代KMT才一度倒向纳粹德国,训练德械师,组织蓝衣社,张学良“相信只有法西斯能救中国”。如果不是随后的中日战争使KMT和纳粹分道扬镳,珍珠港后美国影响大增,中国可能让蒋领导下走向法西斯化了。
- KMT上台后,虽然也号称继承满清版图,但因为抛弃北洋的五族共和,贬少数民族为“宗族”,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内蒙有德王李守信投靠日本,新疆有三区革命,西藏吴忠信参加坐床典礼被冷遇,略施伎俩宣示主权被藏人当成揩油占便宜。民族政策还不如CCP成功。
- KMT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因为扔不掉孙文民族主义的包袱,对清朝的历史定位一直模糊不清,一边歌颂从郑成功天地会到洪秀全孙大炮的反清“革命”,一边又视满清为中国历史之一朝,尤其是在宣传“抗俄”时,完全把满清当作自己人的政权。
- “国父”的尊号,最早是河南大土匪,孙文封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喊出来的。另外“孙中山”这个名字也有问题,孙和中山分别是他的汉姓和日本姓,党徒一般都称他“中山先生”,恐怕没人会喊肃王府十四格格为“金川岛”吧?
- 高先生是搞政治哲学的,史料功夫明显不够
- 岂止不够,就是没有史料功夫
- 宪法学者哪里管什么史料不史料,要是有史料这一说,社会契约论说山顶洞人一天打猎回来,闲得无聊,用石头在墙上画了一幅画,那就是定了一个契约,于是有了宪法,有了国家,也有了一帮宪法学家,这哪里有什么史料基础?周公天命说那一套,也是孔子这个宪法学家在纪念“周武革命”五百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我们都信了==
- 激进革命的负面作用虽然显著,但对于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说,也只有激进革命的煽动性才能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启蒙动员,为民主共和的实现奠定基础,任何对于统治者的光荣革命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事实上即使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果没有前面的那次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等待查理一世自动推进民主改革,这恐怕是痴人说梦。改革也好,革命也罢,都只是一种方式,其结果是多方因素构成的,而民众的智识程度起着关键的作用。不能用当时的民众智识程度来衡量今日,也不能用一国的民众智识程度来衡量他国民众,说改革和革命哪个更正确。 -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 “用现代的主观臆想去强解历史,给历史负上其不可承受之重”,这种批评对于高教授的解读并不合适。你所说的一切,在《立宪时刻》中均有所体现和考虑。但他政治宪法学角度对历史的解读,不限于历史事件的叙说本身,而是从史料中读出意义,这种意义有时连当事人都并无深刻察觉,比如溥仪自传的描述。考虑到民国继承了清代的疆域和人民(满蒙回藏汉)等延续性,从而获得“正统”以及从建国、新民维度对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的意义,《逊位诏书》的历史价值怕是太久受到无视。高教授也谈到,很多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在时势所迫下签署的,比如英国大宪章或是后来的权利法案,但不影响这些文件本身的划时代意义。就此而言,失败的中国版光荣革命的说法,逊位诏书是可以相称的。
- 写得好。过度阐释的一张纸。
- 顺便说一句,所谓的优待清室条件通过本就说明以孙文为首的激进派在当时没有势力,如果按照孙文的思维,那么民国时期孙殿英的挖皇陵被国民政府不了了之,刺杀孙传芳的凶犯被无罪释放的事情早就发生,清朝皇族甚至旗人被全盘屠灭的事情亦有可能发生,这也正论证了高某论点的有力性,也就是退位诏书是北洋,立宪和清室对激进势力的有力歇制,直到1927年所谓的国民革命成功才无力挟制
又论及所谓清室优待条件之背叛,高某也举了三个事情,一张勋复辟违背了优待条款,然康有为,张勋等则以清室退位是以交付于国人建立民国共和,民国首先背叛搞起帝制,弄得乌烟瘴气,是为民国毁约在线。其次段祺瑞再创共和后,并为追究末帝责任,事实上继续保持优待条款。然第二次冯玉祥逼宫何能代表民国?冯某为北洋叛将,又非当时合法政府首脑,其何以代民国来毁约?所以以清室复辟在先,所以冯某逼宫有理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以南京为首都,正是表明其以集成孙文正统为继承,继承的是南京临时总统,而视北洋议会政治为伪朝,此民国非前民国,冯某背叛北洋后叛投党军,视为逼宫行为为国民党认同为正确,而在末帝看来自为民国背约,乃有挖皇陵而国民政府之不顾,遂有后伪满成立之事实 - 传统兄回来了,可喜啊!
- 带头搞军阀割据的不是别人,正是革命党。辛亥革命采取的军政府模式,都督在民政长官之上,实行军管,本身是革命党学日本对朝鲜台湾大连等殖民地的统治方式,革命党却用来统治本国。但是日本总督虽然权大,不受明治宪法制约,但人家忠于天皇,不会割据自立。革命党就不一样了,李烈钧乃是民国军阀第一人,二次革命的主要动机是国民党都督要保地盘,借宋教仁案起事反抗中央而已,孙文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借口。
- 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最无民主法治观念。借宋案和大借款发动叛乱反抗中央,本来逻辑就很荒谬。假如国民党胜了,袁大头倒了,国民党是不是要垄断政权?以前怕袁世凯治下司法不独立,审理宋案有偏颇,那国民党上台后再行审理,自己会不会干预司法?善后大借款合法与否,应该由国会判定。现在国民党用枪杆子强迫大家承认大借款非法,宋教仁是被袁杀的,谁不同意就是袁党,就是假共和,那还要国会和法院干啥?还要舆论干啥?
- 孙大炮的确毛了些。
你看他自己针对黄兴质疑的辩解,都很没底气嘛。 - 牛逼啊 这本书都收到了
- 我在万圣原价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