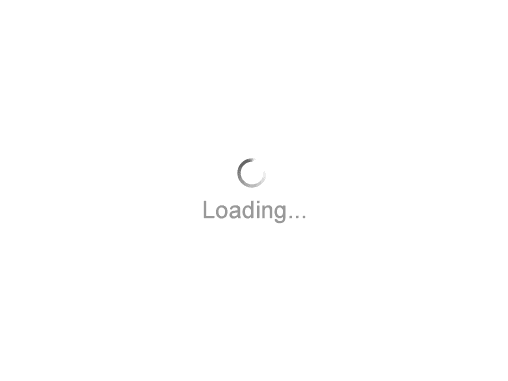迷樓:詩與慾望的迷宮
出版时间:2006年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宇文所安 译者:程章燦
Tag标签:无
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前面看宇文所安的书,有《追忆》《宇文所安自选集》《初唐诗》《盛唐诗》,现在只还剩下些印象,个人感觉《追忆》是其中最好的一本,作者的个性、分析都凸显的很好,由小诗、小情景而引入一个很宽广的的视野,可以看出宇文所安沉溺于诗中很深并很有所得。宇文所安所写的唐代诗歌史我读得并不很完整,可感的地方不太多,其中对诗人的评价、背景和在当时历史中的语境有独到的地方。读宇文所安在看田晓菲的书之后,一时很对胃口,就一直看下来,不过其中也略有瑕疵,但是仍然是很不错的研究,甚至是非常的才气,不拘谨,文笔也是一流,有我喜欢的气息在。
《迷楼》这本书我看得并不是很明白,其中引述的感官、欲望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不大喜欢,而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并且我对国外的诗也很陌生。书中讨论中西诗歌中的爱欲问题,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对诗歌的熟悉度、挖掘、识见都不错。其实只就主题、内容而言,无论涉及到什么,都是会很普通,但个人的体验、思想的积淀注入其中,再熟悉的东西也会鲜活起来,这也是宇文所安的特长。
现在读诗的人不多。我认为诗是“慢”的艺术,若不能静下心来,就不会体会出其中的意境、滋味和深广。幽微的东西、想象力离现在的人越来越遥远,一流的诗人越来越少,能进入诗的内核并有所感的人也越来越少。宇文所安的意义就在这里,一个不错的向导。因为诗也不是自明的,时代在远逝。
诗歌是付诸感官和意象的,如果用理论来解释,难免会有抽离和背弃。以迷楼来作喻,相对于诗的写作和阅读,都如置身于与一个欲望、迷离、游戏的处境中,“在迷宫里,一个人总想走出去,在迷楼里,个人却尽情享受留在里面的经历”。
宇文所安的《迷楼》写出了诗歌的一种传统,即直述感官、透出欲望的这一类型,而这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中并非主流,作者从可能性和诗歌可能具有的意向性来阐释,我觉得是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宇文所安说:“诗歌的游戏使思考困难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得我们说出在“严肃”话语里无法言说的东西。“严肃”语言的种种习惯迫使我们把事物归纳进熟悉的范畴,作出司常见惯的寻常区分;诗歌则允许我们看到在“严肃”话语里被迫压抑的各种关系。在西方传统中,诗歌有时被视为“严肃的游戏”。”如果用理性和抽象的逻辑来思考,其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有时我更相信直觉和感悟,由自然状态中得到的更与自己、现实相贴近。关于“游戏”的内涵,田晓菲在前面的《留白》中提到,我很自然的想到“后现代”的一些讨论。如果把“游戏”看做不认真中的认真,还真是很妙的一种姿态。
诗歌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 200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五,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正在给学生讲中国唐诗《长恨歌》。突然有个学生递上来一张纸条:“请问教授,杨贵妃的洗澡水里放了什么东西,才使她洗后‘侍儿扶起娇无力’?”宇文所安的本名叫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是国际汉学界首屈一指的唐诗专家,但是他却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苦笑着说:“实在抱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可以回家问我妻子。”宇文教授的妻子是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国内盛极一时的“北大神童”田晓菲,现在也是哈佛教授。当天晚上,田晓菲告诉丈夫,杨贵妃洗澡水的古代名称叫“兰汤”,是用多种天然香草和名贵香料煮过的水,所以“水滑”,而中国的香草比如兰草、艾叶、菖蒲、柏叶等经过高温煮沸,其中的药性成分挥发弥漫,吸之过多会使人产生轻微的不适,这就是导致杨贵妃“娇无力”的原因。
- 尽管我有所避讳,不称这些陆续冒出来的汉字组成的团体为“书评”,但是在未来的读者心目中并不能达成共识。对于一篇文章(我更乐于叫“文学作物”),人们总是想找到一种辨识办法,将其体裁叫出来,就好像从芸芸众生中找到了一支醒目的小分队。于是,我要下一番功夫,使读者意会到它还是别的什么。
显然,它不是为仅存一日的报纸副刊而写,也不是营销学的分支,从一开始,它想做的就是找到使自身延年益寿的秘诀。当然,《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这本早期著作的生命力顽强与否,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如果以同舟共济的立场去观察另一位乘客,或这艘驶向未来的船,就会发觉“书评”的本性。
这项工作的目的不包括向陌生人和亲人推销一本书、一个奇妙的观念,尤其不是把芳香介绍给从未涉足这本书的人,与其说在随机地找一些潜在读者,引导他们去看一个究竟,不如说我在自娱自乐:跟自己的记忆力进行一次野外赛跑。最合适的读者本应是宇文所安,然而,他没有必要了解我此刻的想法,即便我是一只令人好奇的孤悬海外的荒岛。尽管如此,我并不垂头丧气,而是在自我告诫:与他一同分享那些被抚弄的芳草所蕴含的干劲。说到底,这项工作的初衷在于自我说服。
那些值得为之动笔的“书”应当是无法竭尽的信息,而紧随其后的书写活动无非是验证人类多数工作的毫无疑义,这一工作反而是有趣的。这项工作可否真实地反映出一位用心的读者在展览一本书时,随着页码的增大,他的兴致与精力不断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在哪些页码上停留时间最长,在哪里又匆匆忙忙,在何时他大体掌握了“书”的形象,并能预测它之后的命运?这本书所显示的信息与无法显示的、有意隐瞒的信息各自占据怎样的比例,“所显示的信息”中得到正确理解的成分有多少?又该如何判断理解的“正确”?
于是,它发出新的命令:“再读一遍!”只有与这本书的作者保持相近的鉴赏力,才有机会与之平起平坐,才不辱使命,否则,就必须节外生枝,蜻蜓点水般地掠过这张巨大湖面,寻找自身的合法栖息地。
如今谈论诗歌,好比是从事一项不合时宜的活动。跟随《迷楼》去畅游昔时诗歌的境况,就好像有人在夜里伴你行进,为你壮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某一时刻:在那里,“诗歌”作为争执的对象,作为左右阵容的分界线,为我们讲述历史风云。宇文所安正是从“某一时刻”开始自己的主题,犹如他插足于过去时代的一场辩论会,一边旁听,一边将满腹经纶整理干净。
与另一些场合不同,他并不从“诗言志”这一东方思想入手,而是从柏拉图的警告启程的。他快速制造了甲和乙两种立场,然后富有见地地逐个解释,其间还不忘考察分类标志是否可靠,他会顺带提及另一组分类:丙和丁。但并不为之深入。在他高谈阔论,就要引人入胜之际,他会反唇相讥,立即摆脱刚刚得到的安全感,把好不容易跟上步伐的读者置于再次迷失的处境。
“但是诗歌确实会引导公民误入歧途。它可以说一些甜蜜的、诱人的话语,打动我们,让我们潜移默化。在正规情况下,我们称诸如此类的事件为迷失,我们能够隐约认识到这种迷失中包括着从令人厌倦、老生常谈式的社会价值观中越轨而出的快感,而当有人问起我们,我们总是大声重申我们对那些价值观是信守不移的。”
“歧途”是什么?“正途”又在何方?诗歌的引诱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人惧怕这种引诱?他为我们介绍“诗歌”为了谋生是怎样变成交际花的。他看到过一张协议签订的全过程,“诗歌”在那张法律文书上按下了手印。仿佛正统的历史篇章就这样形成了,但是,他的建议是:“我们打算腾空博物馆中所有的抽屉,将碎块断片全部摊在地板上,然后以令人愉快的组合方式将它们重新拼装,从中创造出奇妙的故事。”
是的,我们要钦佩他的介绍信上的彬彬有礼、错落有致,但是我们无法预知他会给予怎样的范例,这些范例在服务于主题的前提下是否严格遵循时间秩序。于是,我们不便捞起裤脚、捋起衣袖,从中协助一番,只好伫立一侧,听他介绍一首诗的部分段落如何引起后代读者一层浅浅的蔑视的笑容,并对他“我们要挖掘这层笑容的根源,追踪牵动肌腱扭动皮肉的脉动力量的来源”这一决心表示信服。
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一首诗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它是个人对公众的回应。”每首诗要么是对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抛弃,要么是奉承,但都关乎人生态度。这一结论的得出基于后代读者的立场,也许诗的原作者并不这般认为,然而,当他面对“散落在博物馆地板上的碎片”,并俯身拾起它们时,就陷入了一种交流之中:诗的作者已经发言,这次交流更多的是在读者自身一分为二所形成的两个人之间进行。我们为能猜透诗的本意而欣喜,也为拥有一种重新拼装的才能而兴奋。
他总能轻易地取得我们的信任,他矗立在诗与我们之间,好比是我们消化食物的胃,在使我们可能成为诗的出色读者之前,招引我们先成为他的忠实读者。我们是读者的两次幂。我们常常感激他充任了开路先锋。这要归功于他非凡的挖掘才能,而且从采掘到各种碎片身上,他立即看见了、听到了它们满身是嘴以及嘴角上凝固的唇语,他竭尽所能地说服我们相信它们在讲述一直未终止的古老话题。并且,他造成了多个悬念,却不打算交给我们一张风景区的鸟瞰图。我们被招引进去,但即使我们中途抽身而去,他也允诺不会有任何损失:这本书的上下文关联并不重要,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开始默读。他的优势与魄力正好在于平均地分配思想的锋芒。
诗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儿有一张处方,可以医治百病,他并非开具它的医生,而是它的介绍人——他在利用各种手段阐明它的性质。他首先是一位好的读者,具备了从一行字所占据的视野中发明其新鲜意思的能力,一眼就看见了其中潜伏的引擎,通过发动它,为他的读者缓缓讲解各种隐情。当他慢条斯理、穿针引线地介绍其中阴晴时,我们不由得同意这正是诗之本意——现在,我们也是这般想的,而以前我们没有注意这么多。
“没有注意这么多?”难道诗中果然有一些量化指标,借助合适的方法,就能找到它们?在占为己有的同时,我们不禁麻痹了思想,以至于产生一种失望情绪:从此之后,恐怕再难从这首诗中找到新的乳汁。他几乎穷尽了这首诗的实际含义和潜在含义,但幸好他不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深入其中,从而留下了机会:一首诗是如何形成目前这个样子的?这一问题他涉及的并不多。
在阅读中,我们务必跟上他跃进的步伐,了解到他的动力与动机,尤其关注他的挖掘工作是否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刹那间就占有了一块领地,既是“属于我的”(mine),同时也是“矿藏”(mine)。看上去,他永不疲倦,总能找到迂回的小道。现在,一地的碎片,既有东方的,又有西方的,他开始讲解,煞有介事,滔滔不绝,一方面使我们见到他的博学不仅仅是偶然事件构成的,另一方面他狡猾地推销出他在碎片中发现的关联,并使我们同意他是尽心尽力的讲解员的不二人选。
如果他再放慢脚步,聚集在碎片上的信息没有一丝一毫能逃脱他的视线。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该去往何方,我们正忙于小结他的华尔兹舞步。他招引我们参与一次又一次考古发现,但不允许在场的其余人表态——实际上,他一个人所说的胜似在场的其余人的心声之和。他比任何人都心细,在自己的语法体系中颇具耐心地吐露,这种奇异的品质具有如此的魔力:他的读者偶尔发现的新事物很快就被声明早已归他所有。所以,我们在阅读中正经历一次次角斗,以突破他的束缚,取到不为他涉及的重要证据,来验证阅读的力度:而这给挖掘和拼装工作整体上造成了增益的效果。
我们不禁反思:他的博闻强记确实使已到手的碎片发出奇妙的声响,但是,我们不免认为,这只是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佳说明,而条件一旦改善,比如更多碎片的出土,就可能使他辛辛苦苦编织的网有不小的破绽。我们似乎看到他在窗前玻璃桌上将事先抄录的资料(或打开记忆中的某些书的褶痕)逐一移入他的写作文稿之中,对于这一织补、缝纫工作的能力,他深信不疑。于是,我们又看到:在某处,他本可以一竿子到底,讲清船只行驶的形势,但是,为了平衡几条素材都想独享篇幅的矛盾,他不得不铺展开来,迂回前进,花一些精力来贯通这些素材之间的障碍,好像在它们之间存在不少暗礁。
这些被摘录出来的诗句正是“诗的一种抄本”,他认为“诗是可以一遍一遍地抄写下去的”,“诗歌的文本及其诱惑的力量是共有不变的,但是每经过一次阅读和朗诵,招引的条件亦随之而改变。”当我们在这本书上看到这些诗句时,虽谈不上面目全非,但一个个饱满的情感孕育的时刻不复存在了,在这一首首诗的最早读者与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事情已经发生,它们受尽了时光的摧残(或分享了时光的璀璨),并把一份份敏感的、脆弱的报告递交给诗的最近一次阅读时机。
他为“引诱/招引”设计了一系列的反应,并为这些反应备齐了素材;我们可以看到他周旋其中,自得其乐,一会儿是男人的引诱、女人的拒绝,一会儿是女人的反引诱、男人的空欢喜,一会儿是欲望的一拍即合、半推半就,一会儿是冷艳无情、铁石心肠。仿佛他是两性关系的发明人,并且丰富了这一关系四周的场景:那些稍有瓜葛的景象竞相作为不时之需的隐喻应召而至。显然,他不仅仅是在分析两性关系,他的注意力还分布于这些方面:两段引文之间的关系、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两个行文段落之间的上下文关系、两个爱不释手的观点之间的关系。
有时,我们分辨不清:他到底是在支配这些被挑选出来的碎片,把它们逐一派遣到注意力所在的空间,还是他被这些简洁的引文支配——在它们强烈的授意下,发展自己的思路,不断推陈出新,找到一条条歧路?那些镶嵌在行文段落中的诗行提供了段落前行的动力:关键词。从中我们似乎得出了相应结论:要挖掘这些诗行中的底蕴,非得借助于“无韵的散文”不可。看上去,那些连绵起伏的散文段落是对所引用的诗行的评论,尽管两者结合的初衷在于阐明关于欲望的诸多话题。
第三章插入了不少引文,或可反过来说,有不少段落为了这些积攒下来的语录服务,关于“顽石”这个关键词的强硬推荐,使我们顿时不知所措;事实上,这一章跳过去不读,似乎也没有太大损失,它只是他的思维链条的一个不起眼的环节。
到了第四章,“置换”这个关键词的登场使第一章尾声所及元稹、白居易的通信再次绕梁,我们继“顽石”造成的眩晕之后,毫无心理准备地被拽入新的叙述框架内。“置换”意在探讨一种位置得失所蕴含的趣味,也正好与两性关系中一个古老话题相吻合:喜新厌旧。这一探讨拥有广阔的视域:一方面他可以察看诗中每一个层面、一些重要词语或意象发生了置换与否,关乎到诗的修改、如何保持准确性等问题,也牵涉到诗的性质问题:它是否为言词对现实世界置换的效果?另一方面他还可以触及诗的“传统”话题,对先驱者与篡位者的关系详加分析。考察“置换”问题是他长期阅读所储备的一种敏感反应,是对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密切关注。他把我们带入“隐喻的狂欢节”,使我们相信:“替代的才智变成了言词对自我遭受的物质暴力、对被转化为物的激烈抵抗。”他给予“置换”越多的合理口吻,我们却越发警惕,尽管他对所援引的诗句有符合目的的使用(用渴望的意义替代了整体的意义),或他对“脱离全文背景”进行了自我辩解:“记住,它只是一本书:你高兴怎么读,就可以怎么读。”我们不免揣测,他的心意在于“读”与“写”的置换——哄你开心,争取你的赞同,在给予你阅读合理性的同时,逼迫你接受投桃换李的交易,从而认为“高兴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这一处事原则也合情合理。
当他以“裸露/纺织物”为题阐述各种若隐若现的话题时,实际上在谋求得当的出路:有关欲望的满足与走出迷宫。他找到了方便之门,这是一件无缝天衣,然而,他在钮扣未扣紧的一刹那就看见了丰腴。围绕纺织物的遮掩、有意无意的微微凌乱以及凹凸身体的贴切表示,他纵情探讨了一种简单辩证法的诸多变异。在此,不由得称赞那些适时插入的诗行对应了他的心愿,而且他在化解这些纠缠不休的各种引文的矛盾时显示出非凡的矫捷。如果我们紧随其后,就能发现他对“裸露/纺织物”另有意趣、用途上的发掘。也许一只苹果或橙子也令人看见相应的裸露与遮掩。
在阅读中,我一直想找到他把相应的逻辑植入诗的探讨框架中的蛛丝马迹。难道“言词”正是诗的外衣?他那般谨慎、吝啬,使我始终不得一饱眼福。如果说“置换”所研究的是时间性,那么对“裸露/纺织物”的沉迷就是对空间性的深情。人的身体、水果的身体、诗的身体……都是对位置感的屡屡摸索,都提供了张冠李戴的无限生机。他花了不小的力气用于分析身体有意呈现或躲藏的动机,并紧紧盯住那些情侣在相互呈现之前碰到的情况。所以,当他得出如此判断,我们毫不见怪:“身体及其孪生遮蔽物——艺术和纺织物——唇齿相依。身体需要衣服,以便显露自己(否则,它就要淡出,退回到不受人注意的伊甸园的动物群中);而没有身体的衣服便不再是衣服。”
在他精心建设的叙述框架中,有两种相反方向的目光不断交织:由外向内的张望表明受到了诱惑,或一种视觉伦理的输送,而这正是他所谈及的陷入迷楼之人的处境——这人巴不得长久地沦陷,容忍着自我不能自拔,至于张望的动机与收益,不言自明;而由内向外的春光外泄也好,暗送秋波也罢,讲述的是一种释放与裸露——招引外来者,挑逗未知的时间。也许此举符合迷宫的性质:渴望走出去,以证实身体的活力犹存。
总之,他对“看”的多种变化(张望、远眺、凝视、窥探、对视、俯瞰、观赏……)进行了动机上的层层省察,并把它们统称为一种独特的似是而非的“看”:欲望。尽管他的大多数观察都是基于历史文本,是一种间接的、重复的阅读式的“看”,但是他尽心尽力抹去了这些文本上的灰尘,推开了各种门窗,引导我们看了一个够,同时,这一行为模式正好提醒我们:所有的观看最终落实在类似“诗”的各种文学作品上,都需要一个个壮硕的中介物——有了“诗”,所有目光不期而遇,寓意其中,任人揣摩。
(2006年9月)
- 13岁,宇文所安就被中国的古典诗歌迷住了,从兴趣步入专业领域,用西方理论及华美文笔作学术文章。《迷楼》的文字大概是他文章里绵密柔软的,像一次醺然的迷途。
宇文所安说诗歌设置迷楼。诗歌最初召引和收容的,也许是人的动物性,但诗歌揭示又掩盖欲望,使之更强烈更神秘,在一层薄纱般的阻碍面前,甚至变得更优美起来;沉醉于美,于是人类不能满足于赤裸裸的最后结果,很多人宁愿“迷失”于中途,而引出一条又一条迂回的“歧路”。读者想在诗歌里感知爱欲时,就被种种冒险、想象和追忆所俘虏,最终在自身被唤起的爱欲和美感中“迷失”。
“迷失”是危险的,却几乎伴随着所有类型的审美体验,孔子说“郑声淫”,他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有一种失掉原本状态的危险。柏拉图既赞美诗人,又要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原因一样。
欲望唤醒生命,生命孕育诗歌,诗歌却警醒地避开最后的终点——欲望的挫折、终止,亦即人生的真相。创作者沉溺其中“已惘然”,无法面对现实,就有了许多毁灭、颓废的情事,时见作家深陷其中:日本文学里,不单情死、情伤、虐情比比皆是,唯美混杂着暴力,像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甚至死于自戕。
也许感官、欲望之美,越深入越是无法自拨的吧。这样看来,宇文的阐释,依然是温文尔雅的,他解读着诗艺和欲望中的优美,却对其中的危险点到即止。宇文用接近“魔”的笔法写“着魔”,如果看得头晕脑胀的话,关上书,定定神,跳出来就是。但真的执迷于唯美,可就难以突围了。所以走到极致的文学艺术,也许都是不甚健康的... - 4月3日下午,哈佛大学东亚系James Bryant Conant特级教授(哈佛教授级别中最顶级的一级)比较文学系主任宇文所安亲临鼓楼,为我们献上堪为华章的演讲《说烟:幻想的借代》(On Mist: Synecdoche of the Imaginary)。宇文氏说烟道雾,将古典诗歌中的“烟”加以梳理,发觉其中蕴含的借代、隐喻和寄寓,饶富趣味。讲演中一段关于“金陵烟雾”的,正好契合于大好春光时节,金陵王气之地铺陈排闼。笔者有幸在前排靠讲坛处目睹盛况,不胜荣耀。与偶像(准确地说,加上主持程章灿教授[三联版《迷楼》的中译者],应是两位偶像,看一送一)近距离接触,一睹风采,拍照,要得签名,不亦乐乎,着实成了“追星族”。多亏了宇文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儒雅谦逊,才能让我等“放肆”,而Zizek来访的时候,那架势实在吓人。宇文中文说得不错,但自谦说起来没自信,故采用中英文结合之方式(读诗、必要的提点用中文,其余英文)。现场发了中文文本,文笔曼妙,据说为其学生翻译。当场亮点不断,妙语连珠。特令人感怀的是,宇文说,中国古典诗歌不只属于中国人,更属于全世界。外国人解诗或许每每出现误读、差池,但国人来解不见得便能完全开解个中真味,拘泥于一元诠释或中华中心主义,而排斥汉学的研究实绩,毕竟不是明智的选择。阅读,终究是读者与文本在不同时代境遇里的相遇而生发的点点滴滴。现刊发一篇旧文,以向宇文致敬。
迷楼原为隋炀帝建造的一座供其恣意淫乐的宫殿,炀帝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迷楼如迷宫,“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唐]无名氏《迷楼记》)。
我以为一种好的阅读是必须保持一定距离的,自我的主体性绝不能丧失在作品的“诱惑”里面,尽管我承认投射式阅读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诸多未明之意。阅读中我也力图把自己抽出,贴得太近乃至融入文本之中都会遮蔽自己的视野,如今很少有作品能让自己沉迷。但宇文所安(斯蒂芬 欧文)是个例外。从一读到《他山的石头记》的自序开始,我就迷上了这个哈佛大学的汉学家,不可理喻。宇文所安于自序曰,“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需要‘散文’(essay),因为它已经拥有很多的‘论文’(paper)了”。一篇好的散文应该“entertain an idea”(直译为“娱思”):予人“思想的乐趣”,把一个想法视为一种可能性,无论接受、拒绝、抑或修正,“在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宇文氏接着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需要保持,但是它需要补充,需要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欢迎来访的想法的接待站。”“传统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还是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传统总是在变动当中,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出动现在的神经。”能够读到如此新颖且创意的见解,颇为投缘。因为喜欢,故而从不算丰裕的资本里抠出一部分以收藏他的书,因为想时时地、长期地营造那种沉迷的好感觉。
宇文氏的写作如同迷楼,将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参照的事物放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里,旁征博引,横跨时空,打通古今中西,活用但并不套用流行的西方批评路数,展现出宽广的文化胸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宇文氏主要从个人独特的阅读体验出发,对研究文本进行close reading,严肃认真之中见出轻松嬉戏、充满精湛“思”,在中国古代诗学、比较诗学、中西文论等诸多领域进行富有冒险性和想象性的奇妙尝试与探险。作者在进行“诗”与“思”的对话,享受探险的快感之同时,也给读者奉上了文本的愉悦——我们发现,原来古代文学研究还可以变得如此生动、鲜活,如同鲤鱼跳出水面带起水珠滚滑荷叶。不能保证宇文氏阐发的一切都是准确的,切合原意的,非汉语学界研究者的“误读”(misreading)在所难免,但谁能担保古代之人比今世之人理解作品更为透彻,中国学者比西方学者理解文本更为透彻?宇文氏以其越界穿行的书写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古典诗学的研究风貌,开辟了一道道亮丽无比的风景线,被开辟的疆界渐行渐远延伸向无限广阔的天空。文字华美绮丽——我看的是译文(宇文氏作品的中译本大都由其内子田晓菲翻译或校对)据言宇文的英文十分优美典雅。如此,阅读作品亦如进入了迷楼,不但迷而忘返,而且乐而忘返。
宇文氏以《庄子 逍遥游》里的惠子的大葫芦为比喻,倡议一种“瓠落的文学史”,“一部文学作品不仅应该被放在这种文体的历史里加以讨论,而且它还隶属于一个我称之为‘话语体系’的系统,这个系统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阅读、倾听、写作、再生产、改变以及传播的团体”。于是,宇文氏要努力做到的就是“准确地表述在一个‘话语体系’当中原始材料和文本传播流通的实像”。这就明显地区别于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状态。在这种文学史观影响下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别开新境界。记得在海外汉学方面颇有造诣的程章灿老师说,汉学研究在大陆、欧美以及日本呈现出非常不同的三种面貌。宇文所安大约能代表欧美吧,当之无愧的。这块大洋彼岸瑰丽的石头应当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
对韩愈《南山诗》、李贺《昌谷诗》、柳宗元《小石城山记》颇费匠心的细致比较,展现出宇文氏对中唐 “自然景观的解读”。从韩愈的《雉带箭》诗出发,导向“唐朝的公共性和文学艺术”此等“现代性”的论题。再比如“刘勰与话语机器”、“特性与独占”、“断片的美学”等,皆“集开新境界”。而《初唐诗》、《盛唐诗》等专著独具慧眼、流金溢彩,在一些被看作炒得很烂的领域烹调出美味盛筵来。
在我的推介和带动之下,好几位同学都买了宇文氏的书。能把自己的喜欢与大家分享,真好。 - 看完了宇文所安的迷楼。得承认,我被这本大名鼎鼎的书弄得有些疲倦。一来是读书这一习惯已被久置,二来是甚觉作者的文笔与我波长不符。宇文所安口口声声的“我们”让我很有些无所适从:他代表的是谁、他的听众又是谁?再加上所谓的Essay体——谈不上优美二字(当然很可能是译者的关系),作为严肃的论述又嫌烦琐含糊,太不简洁;颇有呓语横空而起且滔滔不绝之势。我嫌他想太多又说太多,看着不免觉着烦躁。
我以为这书决定性的好处在于选材精当。第一,切入点好,作者选取的是诗中的欲望,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题材,是单纯而复杂的片断,也是颇能体现诗学长处的主题。第二,实例好,他按他的需求,精挑细选出十几篇诗,而这些诗歌不仅在各章节中能独立按此章主题被分析,还能在全书的范围内前后呼应发展,作者对材料的运用可谓圆转如意。所谓“提出了一套跨越时(古-今)、空(东-西)的独特的阐释套路”“(对各家各代诗歌)一视同仁地欣赏”,其实是落实在爱欲这一主题的恒久与通用上的。宇文所安剖析诗歌的凭借点,从一开始就是主题,而非外在的形式。这使得他的话语能更容易被读者掌握并认同,只要是具有常识且逻辑的推断,并不容易引起很多争议。
书凡五章。诱惑/招引;插曲:牧女之歌;女人/顽石,男人/顽石;置换;裸露/纺织物;另加绪论结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第三章,围绕着皮格马利翁这一例子展开的探索,大部分分析清晰而直接。类似“……他的目的(Ronsard, “一百遍我渴望自己能够变形”)是要理解她……但是惟有在想象中侵犯她才能获得这样的理解,这样他就到了一个自我矛盾的边缘,他期盼以强求获得爱情,而爱情又只有当它是自由自愿地给予的时候才成为爱情……这礼物即是他者,但此时它已不再是他者,而只是他自身意图的一种建构。这个艺术即使获得了完美无憾的成功,也已经走向其预期效果的反面”这样的分析,在书中大量出现。事实上,作者所探讨的一切都建筑在矛盾之上,所谓“正是在有破绽的地方,艺术臻于完美无缺,在这种时候,它唤起了既受到约束又失去控制的自然本性”(第五章),这正是作者所关注讨论的中心,而,由于矛盾的本性,使得宇文所安的滔滔不绝成为可能,他尽可以一直讲下去。
在迷楼这本书中,我最为赞赏的,还是作者的组织眼光与能力。能在千头万绪中抓到一些关键,并清理成明晰的脉络进行自己擅长的写作,真是令人羡慕的事情。
- 哦,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绪论了。看惯了刘小枫他们巾头气十足的“诗与哲学”的争论,再看宇文所安谈论诗歌与我们的欲望,飞流直下,目不暇接。
诗歌是怎样嘲笑我们的虚弱,激起我们这些螺丝钉从革命的大机器上脱身的强烈欲望?而共同的价值,又如何…………………………(待续)
(计划中的最后一句,另起一段)桃花多处急抽身。 - 读《迷楼》后,写给姑娘的诗。
我会教它们如何对你说
你就可以知道我想让你听
如果,使唤春天的鸟儿,教会每一只一个字母,就能拼起你的名字。如果,一句话,从初冬日讲到雪融,姑娘来了又去,头发长了又长,总有一天,你就明白我的言语,其实是极贫乏,又极简单。我根本爱你,根本是企图从你的形式里,找到自己(歌德语)。
我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抵挡 正如
这个春天 它们在身体里播种
而渴望文字的手正如渴犁的贫农
别回头 我的爱人
过去在来路上裹着死亡的尸衣 步伐繁冗
我不能回头 我不能看见你的身体
被任何悔意击中
(这是俄耳浦斯,去救他的妻子
那传信的神 他
站在有所逼迫的来路 于是)
我们不能重返 我们必将前行
这故事属于希腊神话。俄耳浦斯脚步匆匆。他名字拗口的爱人和赫尔墨斯——掌管死与通信之神立在一起,裹着尸衣的脚步拖拖沓沓。他们走小路,他们在一起,两个爱人,一个神,两个活人,一个死人。这是一个交易,俄耳浦斯扔掉回眸的权利,死亡便不得不从爱人的躯体上退席。然而,各位,拐一个弯,他仍然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请问怎么能不叫忠诚的爱人,回头去注视一眼她脸上的红晕?整个森林里都是叹息,赫尔墨斯,他也垂下眼帘。唯独不叹息的是爱人,巨大的死亡,把她罩得严严实实。死亡是她的全部遮蔽。她不知道曾经有所希望,更不会有所懊悔。别回头,别回头,否则叹息和泪水,全部属于俄耳浦斯。
别回头,别回头。
事到如今 我的力气已经耗尽
但愿我能宠你嬉笑 听你言语
我大概只能爱你如一豆台灯
我从夜里把它偷偷运走
我看你亮在别人的床头
我不能言语 必将前行 不可回头
我爱你如一杯凉的柠檬水
但笑是不凉的
我爱你是徒劳 是旋转你的面前
好心的大人!
请与我共舞一曲
小米,以及愿意读诗,说诗的你们,请听我说。我觉得写诗是一个与文字背道而行的过程,我追求的病态的简约,在诗歌中全部成形。我只能祈求,那些不因我意愿出现的语词,可以如我所愿地拖长语言的节奏,让它不再那么猴急。当它们分行地,陈述地铺开时,在段落中看似从容的节奏,忽然显出力不从心的局促来。
诗果然是检验我们文字的有力武器,而火是我们文字的唯一归宿。我只能努力教那些文字说了我想说的,也许这样,你就能听见我想让你听的。可惜我们不能回去八岁,那个与神和自然更为接近的年龄,在那里你爱我只需一咧嘴,我爱你老是笑个不停(小米语)。
- 不得不佩服这些老外汉学家,他们的思路是那么宽阔,又是那么地沉迷于自己的研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古代的诗歌美学。
- 奇怪这是给一星的原因吗
- 翻了,没细看。印象是:喜欢。
- 宇文的书,我想更多的是“好玩”,有趣,富有启发性,要说多有深度是比较难的。
- “内子”是称自己的夫人时用的,难道你是宇文所安?
- 绝倒,这个特级教授的称呼太喜感了,就是校级的讲座教授,哈佛最高教职
- 迷楼之后,看完了追忆、初唐诗和盛唐诗。
追忆和迷楼的写法差不多,不过选材范围小,解析也不多生枝节,比较清晰。虽然对于材料的理解错误继迷楼后再次出现,不过总体来说,作为非母语的研究者,真是很不容易了。
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一个美国学者能深入研究中国诗歌到这个地步,简直让中国读者都觉得惭愧起来了。我想中国的读者,虽然更容易体会本国诗词的美感,却也容易由于惯性而产生钝感与惰感,并只按自己的口味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记诵。初唐诗书中有些例诗文句佶屈聱牙,又或是千篇一律的应制诗,要我作为读者,是看都懒得看就直接跳过的,想想国外做学问的人怎么费力气一字一句地去理解,就觉得很了不起。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关注点的不同。在中国被竭力强调的所谓“诗眼”、“警句”,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很可能没有太多效力。宇文所安关注整体超过片断,不论是单篇诗歌,还是整部诗史,都是如此。他追寻的是脉络、逻辑、整体,而对于母语的读者来说,对诗歌的片断的心有灵犀,应该才是读诗的趣味与意义所在。 - 我不知道是我没看懂,还是翻译问题,目前看到第四章“置换”的第一段就开始犯迷糊,作者的话比那“九歌”令人费解得多了。接着再往下读,几页纸翻了好几遍,还是不明白。
- 也认为这本书结构设置确实很独到,而在比较解析时实在难吸引人,大概书者太过于沉迷语言自由,忘记或者不想顾及阅读的人,又或者这根本是译者的问题,哪怕是那个特殊的田晓菲。
- 旁征博引得我有点晕糊~~~
- 嘿嘿。。。扒拉老吕的旧坟。。。甚是开心
- 挖坟
- 你想说的是【头巾气】吧……还是你一直以为是【巾头气】?
- 这篇烂尾了,我想删
- 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