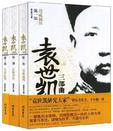袁世凯三部曲(全三册)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线装书局 作者:侯宜杰 页数:共三册 字数:1800000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袁世凯,一个有血有肉,兼具隐忍、智慧、多情、梦想并曾经胸怀天下的盖世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急躁、残忍、狡猾、狐疑,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置人于死地的乱世枭雄。 有人说他骨子里浸透着无赖恶棍习气,心黑手辣,心机深沉。也有人说他敢作敢为,提得起放得下,堪称天下奇才。 有人说他只会夸夸其谈,厚颜无耻。也有人说他办事认真,不徇私情,机智多谋。 甚至有人特地亲题对联以赠: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在一个群雄并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也曾脱颖而出,并带给中国巨大的影响。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有过怎样辉煌的时刻。洋洋百万字的作品展现了一代枭雄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杀伐、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它不仅是上上乘的史学经典,更是兵法谋略、政略宝典。在曲折生动,卷帙浩繁,墨香四溢的巨著中,体味袁世凯那真实的一生……
作者简介
侯宜杰,1938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袁世凯全传》、《百年家族——袁世凯》等。发表的文章有《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论清末立宪的进步作用》、《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
书籍目录
第一部 逞威属邦 一 弃书学剑 如鱼得水 二 属邦传警 整饬军纪 三 诱擒太公 剿除余党 四 头角崭然 狂妄跋扈 五 蜜云欲雨 锋芒毕露 六 灰心请假 充光调人 七 走马上任 正名定分 八 穷究附俄 建言废王 九 窃玉偷香 兄弟反目 十 压制自主 风刀霜剑 十一 暗纳小星 贷款示惠 十二 防制日本 智绝力穷 十三 屡乞回国 仓皇逃归第二部 宦海浮沉 一 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 二 督练新军 有惊无险 三 观察行情 叛卖求荣 四 剿团保教 晋升直督 五 推行新政 改换门庭 六 窥测风向 左摇右摆 七 鹊巢鸠占 参与立宪 八 狼狈为奸 排除异已 九 两面三刀 罢官回籍 十 貌似隐逸 野心不死 十一 东山再起 待价而沽 十二 翻云覆雨 只为权势 十三 无情逼宫 清朝寿终第三部 总统皇帝 一 拒绝南下 嗾使兵变 二 逼走总理 组阁生波 三 枪毙张方 礼迎孙黄 四 赣下碰壁 沪上流血 五 否认谋刺 悍然用兵 六 胁迫选举 摧毁共和 七 集权复古 态度暧昧 八 对日交涉 原形毕露 九 强奸民意 接受帝位 十 内外交困 众叛亲离 十一 撤销帝制 呜呼哀哉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一、弃书学剑如鱼得水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天空蔚蓝,阳光灿烂,和风频吹,带来一股湿润的海洋气味。一辆马车出了烟台西门,沿着近海的官道向西疾驶。车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位二十三岁左右,五短身材,略显粗壮。头戴一顶青色瓜皮帽,身穿一袭青绸夹袍,外罩蓝缎大褂,脚蹬一双轻便布鞋;长方脸形,五官端正,二目炯炯有神,脑后垂着一条辫子,看上去倒也不俗,但却掩饰不住纨绔子弟的轻浮气质。此人就是袁世凯。另外两人都比他年轻,一个是他的家仆王成,一个是乡邻赵国贤。袁世凯字慰庭,别号容庵,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公历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寨,所以后来人们也称他为袁项城。在咸丰、同治和光绪初年,袁家楼房瓦舍连成一片,拥有良田五十多顷,开着几处典当铺,广有财产。他的二叔祖袁甲三官居漕运总督,堂叔保恒在朝中做到侍郎,富贵显赫在项城乃至陈州府一时无两。他的父亲名叫保中,叔父名叫保庆,属于长房。袁保中有一妻一妾,都姓刘,元配生子世敦,后来得病去世。他又把侧室扶正,作为继室,继室生了世昌、世廉、世凯、世辅、世彤五个儿子。袁世凯呱呱坠地的时候重达七斤多,刘夫人的奶水不够他几口吃的,没有了就哇哇大哭,任怎么哄也哄不好。刘夫人为此愁了好几天,忽然想起来弟媳妇牛氏的孩子刚死不久,奶水未回,极其充足,便让牛氏代奶。由于没有儿子的缘故,保庆夫妇喜欢得不得了,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得无微不至。世凯能够吃得饱饱的,就不再哭闹了。如此过了五年,保中见弟弟深爱世凯,年龄已近四十,仍然没有儿子,恐怕他绝了后,断了香烟,便把世凯过继给他。从此,世凯就随保庆夫妇一起生活了。同治五年(1866),袁保庆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后来调到江宁(南京),都给世凯聘请了有名望的老师,让他好好读书。但他从小过惯了娇生惯养、寄生安逸的生活,到了歌舞繁华的大城市,更是目迷五色,心猿意马,加以性格喜动不喜静,不论老师如何督促,也不好好学习。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病故,他便同母亲牛氏等人扶柩返回项城老家了。以后他跟着堂叔保恒、保龄在北京读书,仍不认真,学了很久,文章尚不入门。光绪二年(1876)秋天举行乡试(清代三年举行一次的考试,考中者为举人),他回河南应考举人,结果落第而归。同年九月,他在家乡结了婚,娶了一位沈丘县的富家女儿于氏为妻。过了两年,袁保恒在开封帮办赈务,不幸得了传染病去世,这个大家庭的矛盾日渐突出,便各自分居。世凯分得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成了一家之主,像匹无羁的野马,愈益放荡不拘。为了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他还发起组织了两个文社。光绪五年(1879)秋天,他再次参加乡试,还是名落孙山。他又羞愧又气愤,赌气把过去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向人扬言:“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怎么能够龌龌龊龊地长久困在笔砚之间,自误大好光阴呢!”他感到通过科举向上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决心另外寻找一条升官发财的途径。在家待了两年,他一事无成,并且得罪了族人,与妻子于氏也成了一对怨偶。正在极端苦闷的时候,上个月忽然接到继父的盟弟吴长庆的来信,要他前去山东登州,他便毅然离开家乡,带着家仆王成和愿意投军的乡邻赵国贤北上,先到天津见了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的堂叔袁保龄。叔父同意他去投奔吴长庆,临行给了他四十两银子。他们三人坐船去了烟台,在烟台下来,吃了早饭,又乘坐雇来的马车,驶向登州。下午三点多钟。登州水城提督署内的花厅中,一张漆得发亮的红色桌旁,围坐着六位身着便服的人,他们很随便地喝着茶,吸着烟,说着闲话,气氛无比的融洽。坐在上首的那位就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身体颀长,面孔白皙,唇边蓄着浓密的短须,五十出头的年纪,风度潇洒,眉宇间透着几分威严和刚毅。别看他外表像个恂恂儒士,却是一位能征惯战的虎将。他早年读书,在家乡办团练,不久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收编,后来为淮军统帅李鸿章的麾下。光绪六年(1880)奉调帮办山东防务,亲率六营从江宁移驻登州府,将行辕设在了府治所在地蓬莱县的水城。来到这里已经两年,重要的军务早已布置就绪,平时除了日常公事,他不是读书,就是同幕僚谈古论今,下棋品茗,今天在座的五位均是文案上的夫子。坐在东面的那位瘦高个儿,额头宽阔,鼻直口方,两道浓眉下生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姓张名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幼年读书聪颖过人,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先生看见有个武官骑马从门前经过,遂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其对出下联。他不假思索,顺口吟诵“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喜,从此有神童之名。他中了秀才,县里府里各种考试,无不名列前茅,但说也奇怪,就是考不中举人。后来因为家中贫困,应聘为江宁发审局孙云锦的书记。爱才礼士的吴长庆发现了他的才华,想方设法把他邀到了军幕,只让他办理机要文书,别的事情一概不管,以便让他有时间读书应举。并特别在堂后盖了五间茅屋,作为他读书兼办文书的处所,每月给二十两银子的薪俸,极为优礼。他对吴长庆也投桃报李,尽心竭力出谋划策。现在他只有二十九岁,已经成为幕僚中的首要亲信。他的三哥张詧也在庆军,主管支应所,负责钱物。坐在西面靠北的那位,中等个儿,浓眉大眼,姓周名家禄,字彦舁,江苏海门人,文才声名,跨县越州。靠南的那位叫林君实,字怡庵,福建人,三十八岁,在幕府中年龄最大,因怀才不遇,才入军幕。并坐在南面的两位,一位肤色较白,名叫朱铭盘,字曼君,泰兴人。另一位肤色较黑,名叫束纶,字畏皇,江都人。都是张謇的同乡,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闲谈了一会儿,话题是知人难,交友也不易。吴长庆吸过水烟,喝了口茶,感慨良深地讲了他如何与袁保庆结交的故事。那是咸丰四年(1854)八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了安徽大部。吴长庆的父亲招募了三千乡勇,乘太平军不意,一举克复了庐江城,但立即又陷入了太平军的包围。坚持了几天,粮饷乏绝,岌岌可危。吴长庆奉了父亲之命,单人匹马闯出重围,向统领大兵的袁甲三求救。他好不容易到了袁甲三的庐舒大营,把危急情形讲了。袁甲三即问儿子保恒和侄子保庆有何意见。保恒认为面临强敌,兵贵集中,不宜分散,否则大营危险,何况援救未必济事,不主张出兵。保庆则认为绅士力弱不支,孤城垂危,前来求援,理应发兵相救。袁甲三听了他们的话,反而拿不定主意,迟迟不发救兵。结果庐江失陷,吴长庆的父亲阵亡。从此他对保庆的朴实厚道,深明大义,急人之难,衷心佩服,并与保庆换了帖,结为异姓兄弟,赤诚相待。以后他们同在江宁,来往日密,情谊日笃。保庆病逝的时候,其子世凯年纪尚幼,他代为料理了后事。诸人听了都很感动。稍停,吴长庆又说:“说到这里,兄弟还要告知各位一件事情。前时我给世凯去了封信,让他前来,以报答盟兄的隆情高谊。他若前来,想必就在这几天了。”张謇说:“大帅对世凯加意栽培,克尽朋友之道,袁保庆英灵有知,当可告慰于九泉了。”吴长庆微微摇头:“我不想让世凯在营中效力,只想叫他安心攻读,博得一第。”束纶接着说:“如此更好了。”环顾大家一眼,吴长庆说:“世凯来读书,全靠诸位指教。不过也用不了这么多先生,有两位足够了。兄弟想请啬翁、彦翁偏劳,未知肯赏脸否?”张謇忙说:“大帅吩咐,理当效劳。只恐才疏学浅,误人子弟,有负重托。”周家禄也谦逊了两句。吴长庆朝二人拱拱手,表示谢意。说:“二位不必过谦,就请费心教诲。世家子弟多不上进,管教应当严一些,切勿顾及情面。”这时护勇头目曹正明走进,向上屈膝躬身,右手下垂,打了个千:“禀大帅,有个河南项城来的袁世凯带着两个人求见。”“领他们进来。”“喳。”曹正明躬身退出。朱铭盘笑道:“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大家都笑了,起身欲退。吴长庆抬手制止:“各位别走,先见个面,以后也好说话。”大家复又落座。少顷,曹正明领着袁世凯等来到,吴长庆望见,立起身来。袁世凯急趋几步,跪下磕了个头,说:“侄儿世凯叩见叔父大人,给叔父大人请安。”吴长庆笑容可掬:“贤侄请起。”袁世凯爬起身来,忙令王成、赵国贤上前叩见。王成和赵国贤赶紧放下东西,跪倒磕头。待他们站起身来,袁世凯指着他们对吴长庆说:“这一个叫王成,是小侄的家仆。那一个叫赵国贤,是邻人的孩子,他听说小侄要来,非要跟着前来投军不可。”吴长庆遂向他引见了张謇等人,他逐一作揖,大家还礼,然后坐下。吴长庆令人送上茶来,问了他母亲安好,又问了些路上的情况。袁世凯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一一回答了,并将带来的礼物奉上。张謇等人退出。曹正明听了吴长庆的嘱咐,也领着王成和赵国贤离开了。吴长庆打量了世凯一眼,笑道:“记得令尊谢世的时候你还很小,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真真令人欣慰。”接着问:“平时在家做些什么?”袁世凯恭敬地回答:“在家自学。”吴长庆笑问:“可曾进过场?”袁世凯闻言把头低下,满面羞惭,不好意思地说:“侄儿愚笨,两次下场,均未考中。”吴长庆笑道:“不少秀才多次进场,仍未中举。你才考了两次,不算什么,只要埋头苦读,总有高中的一天。”袁世凯不自然地应道:“是的。”吴长庆捋捋胡须,和蔼地说:“我唯恐你在家荒废了学业,特让你来安心攻读。这里的几位夫子,均为饱学之士。我已经同张先生和周先生商定,你读书由他们指教,文章由他们改正,比在家自学强得多了。至于名义嘛,可在文案上给你挂个名,每月十两银子的薪俸,伙食费由我另外拨给。原来我想派两名亲兵照料你的生活起居,你既然带来了王成和赵国贤,就给他们两人补个亲兵,让他俩照顾你吧,饷银也从我这里拨给。几位夫子办公住宿都在云昙庵,那地方环境清幽,你们也住在那里,以便随时请教,你看好不好?”袁世凯满怀希望想弄个差使干干,没料到吴长庆又叫他走最厌恶的科举之路,有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凉了半截。可是他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心意,显得不求上进,没有出息。脑筋速转,计上心来。连忙回答:“叔父大人的厚爱,侄儿铭感五内。只是侄儿从小喜欢走马试剑,可否一面读书,一面当差,学些实际本领,以备异日报效国家。”他想此着有效,以后就有办法了。吴长庆严肃地说:“令叔祖、令尊等不是进士就是举人,你也应该走科举这条正途,方才不负他们的期望。一心不能二用,明年是大比(即乡试)之年,你必须专心致志地攻读。”在这位尊长面前,袁世凯有苦难言,勉强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答道:“叔父大人训诲得极是,侄儿一心向学便了,但有一事不明。”“何事?”“侄儿是否正式拜师?”“不必,他们不会接受。不过你要虚心求教,像师长一样地尊敬他们。”师生名分极重,袁世凯最怕拜师,受其拘管,不拜师就随便多了,听了没再言声。以后曹正明进来,吴长庆令他带着袁世凯和王成、赵国贤前往云昙庵安置。第二天上午,吴长庆领着袁世凯去见张謇和周家禄,交代完后就到签押房去了。张謇望着袁世凯说:“筱公既然将老弟台读书的事情交代下来,我们只得勉为其难,但确实感到惶恐,怕误了老弟台的前程。”在私下里几位夫子都亲切地称呼吴长庆为筱公或者筱帅。袁世凯慌忙站起来说:“老师这样说,弟子担当不起。听世叔大人说,老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播遐迩,还请不弃弟子驽骀,费心教诲。”张謇说:“筱公过誉,不可当真。以后我们共同切磋,互相策励,总期有所进步就是了。至于老师云云,那是万不敢当的,免了吧。”转脸问周家禄:“彦异兄,你看呢?”周家禄一向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性格爽朗,说话诙谐幽默。闻问不住点头:“是啊,是啊。我们也未中举,年龄不过痴长几岁,怎敢妄为人师?再说慰庭乃名宦之后,世代书香,家学渊博,说不定捷足先登呢。”说罢哈哈一笑。张謇听了不禁莞尔。袁世凯面孔略窘,马上恢复常态:“老师如此说法,让学生汗颜无地了。”张謇适时转过话题:“慰庭新到,需要休息,不妨各处走走,读书的事过两天再议不迟。登州虽小,可是历史悠久,值得游览的地方颇多。我们所在的这个水城,就够看上半天多的,今天我们就在里边转转,不知慰庭是否有此雅兴?”一听游玩,袁世凯劲头十足,忙说:“正要跟着老师学习。”出了云昙庵,三人沿着小道迤逦上行,一路苍松翠柏,繁花似锦,燕语莺声,赏心悦目,有节奏的海涛声不断传来,如同一曲深沉雄浑的乐章。在唐朝所建的龙王庙观赏了一会儿,他们去了天后宫。此宫高有数丈,殿宇雄伟,内中供奉着一位栩栩如生的女神。袁世凯不住赞叹,而又不知道天后的来历,不禁发问。周家禄告诉他:“是宋代初年福建莆田人都巡检林源的女儿。此女仙去以后,被人们尊奉为海神,历代香烟不绝。本朝康熙年间,先封天妃,继封天后。雍正年间定下制度,地方官春秋两季致祭。”侃侃而言,如数家珍。袁世凯问:“天后赐给人们什么福禄?”周家禄答:“人们不过祈求出海的时候风浪不作,平安归来罢了。”游完天后宫,张謇指指上边的巨阁:“此乃当地观海的最佳之处蓬莱阁。”说罢前行。蓬莱阁共有两层,雕梁画栋,檐角飞起,风铃叮咚,比天后宫巍峨壮观多了。上层周围摆放着八仙桌椅,中间是八仙醉酒后各显神通渡海邀游的塑像,个个放浪形骸,惟妙惟肖。出了蓬莱阁,他们到了山顶,倚着北边的石栏观赏歇息。袁世凯凭栏俯视,栏下就是陡立的断崖绝壁和浩瀚无边的大海,海水碧蓝,波涛滚滚,一浪接着一浪,涌到绝壁,卷起干堆白雪,激起万朵银花。举目远眺,青山隐隐,白帆点点,顿觉心旷神怡,胸怀宽阔。观赏了一会儿,张謇慢悠悠地介绍了蓬莱阁的历史及仙阁凌空、狮洞烟云等登州的十大景观。袁世凯问:“古书上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蓬莱就是指这里吗?”张謇答道:“三神山就是海市蜃楼造成的假象,古人不明其理,疑有神仙居住,加以方士故意渲染,就有了三神山的传说。有些帝王相信这一套,派人带着大批童男童女东来,到海中寻求长生不老仙药,荒唐之至。”周家禄接着说:“我们脚下的这座小山叫丹崖山,为登州的最高点,水城就绕它而筑。”继而指着城墙说:“城墙之内,就是水城。那是南门,名叫振扬楼。这里宋朝的时候叫做刀鱼寨,明代改设登州卫,因为河口窄浅,海船运送军需物资不便,又加宽加深,用挖出的泥土筑了这座城,并把海水引进城内。后来防御倭寇侵扰,在土城墙外又加砌了一层砖石。那一片房子就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的帅府,现在是筱帅的行辕,营务处也设在那里。”袁世凯赞道:“老师真是博学。”张謇笑道:“他读过《登州府志》,焉有不知之理?”袁世凯方始了然。以后他们游览了苏公祠、三清殿、望日楼、海潮庵、李公祠等名胜古迹,就回来了。晚上,袁世凯给四叔保龄和家里写了信,报告了来后的情况。隔了两天,张謇、周家禄与袁世凯谈话。张謇首先说:“我们商议了一下,你的功课从今天开始。”接着问:“想来四书五经都讲过了?”“讲过了。”袁世凯回答。张謇说:“那就省事多了,以后就按乡试三场的要求努力。”袁世凯木然点头。张謇接着说:“平时你自己读书做文,每逢三八之日出新题,并商榷做过的文章,这办法你觉得可行吗?”袁世凯恭答:“但凭老师吩咐,学生无不遵命。”周家禄说:“你的根底和特长我们都不了解,为做到心中有数,以利进行,我们各出两个题目,你先做做,时间可以放宽一些。”袁世凯呆板地答道:“是。”张謇笑道:“筱公极其关怀老弟台,一心想将你造就成栋梁之才,望你奋勉,不要辜负筱公的美意。”“学生谨记。”袁世凯毕恭毕敬。周家禄将拟好的题目交给他,说:“先去做吧。”回到房间,袁世凯打开题目一瞧,眉头立即皱起,点燃上一支雪茄。他的烟瘾很大,不过不吸大烟,不吸香烟,只抽雪茄。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深思。良久良久,方才提起笔来。过了七八天,他交了卷。张謇强压着心中的不快看完了最后一篇文章,极不耐烦地丢在一摞文稿的上面。几位夫子彼此不讲虚礼,周家禄推门进来,一旁坐下,见其闷闷不乐,即问为了何事。张謇指指文稿:“唉,真想不到。”周家禄朝桌上望了望,疑惑地问:“你是说慰庭太差劲了?”张謇苦着脸说:“可不是嘛!文章芜秽拉杂,删也无从删,改也无从改,简直糟糕透顶,根本不能卒读。我耐着性子看完,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试帖诗对仗不工尚且不说,居然连音韵平仄也弄不清楚。真乃孺子不可教也,不可教也。”说罢大摇其头。周家禄慢条斯理地说:“世家子弟依仗祖辈父辈的荫庇,大多以读书为虚应故事,很少有认真的,慰庭大约也染上了这种恶习。筱公把他托付给我们,我们尽到人事而已,我兄何必为此烦恼?”张謇依然不能释怀,淡淡地说:“世家子弟不爱读书,我岂不知?然而二十多岁,文章糟糕到这种样子,实在太出人意料。这一来,你我可有苦头吃了,筱公的一番美意恐怕也将付诸东流了。”周家禄想想说:“也许他志不在此,所以文章做得不好,他的策论我看还有点意思。大凡世家子弟都有虚骄之气,极爱面子。若是不相干者,我们不必去管,慰庭不同,看着筱公的情面,我们不得不花费些心血。我想不必责备过严,批得一塌糊涂,叫他面子上下不来,但能画几个圈儿,就画上几个,他毕竟不是我们的正式弟子。至于今后的发展,只有因势利导了。”周家禄走后,张謇叫来袁世凯,把文章拿给他看。袁世凯见涂改得满纸皆是,脸色变了又变,旋又挤出一丝笑容,恭恭敬敬地说:“多谢老师费心,学生一定将改正之处仔细拜读,切实体会。”张謇没有注意到他飞快的表情变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说:“做学问一点不能投机取巧,唯有多下苦功,才能有所进步。做八股文章,只要理解把握了题意,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这四股,并不困难。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是正文,议论的主体,而且每股均有排比对偶的文字,既要议论得正确,发挥得透彻,文字也要工整流畅。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熟读四书五经,融会贯通,还应多读名家的制艺(即八股文、时文),学习写作技巧。试帖诗重在音韵和对仗,熟能生巧,多背唐诗大有裨益。此皆老生常谈,关键还在自己。”袁世凯站直身子,垂首答道:“老师的教诲,使学生顿开茅塞,学生一定加倍努力。”在张謇和周家禄的督促下,袁世凯不得不打起精神,刻苦努力。他也真想中个举人,给自己争些脸面。但他的屁股没有坐稳的时候,不是抽会子烟,就是喝阵子茶: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不愿意低声下气地去请教,一怒之下把书丢到一边;碰到难做的文章,他喃喃咒骂,写不上三四行,就撕得粉碎,撕了写,写了撕,一折腾就是大半天。月光皎皎,虫鸣唧唧,涛声隐隐,清风飒飒。袁世凯坐在灯前,神驰千里。赵国贤把一摞文稿放在他的面前。他极不情愿地逐一翻过,见周先生批阅的多为嘉奖之意,圈的圈儿不少;张先生虽然指出较前进步,但应注意的地方仍有很多。他面对窗前的明月,呆呆地坐了很久,思索了很多,结果如同一团乱麻,愈理愈乱。他想大哭,可又哭不出来。从此,他愁眉苦脸,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急得吐血,喉咙也肿了,服了几剂药,才慢慢痊愈,原来胖乎乎的身体整整消瘦了一圈。
后记
我是个史学工作者,根本不具备文学创作的条件,从未萌生过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虑到人们平时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文艺作品,而充斥荧屏的历史剧等又多歪曲捏造,搞得历史面目全非,误导受众,我便一时心血来潮,不自量力,试着搞起历史文学来了。为了省些力气,我选择了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无权改写。历史文学虽然允许虚构,然而既称历史文学,就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创作,使人从中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绝对不能为了追求卖点,任意杜撰。
编辑推荐
《袁世凯三部曲(套装全3册)》由线装书局出版。“袁世凯研究大家”侯宜杰先生,十年磨一剑。有人说袁世凯骨子里浸透着无赖恶棍习气,心黑手辣,心机深沉。也有人说袁世凯敢作敢为,提得起放得下,堪称天下奇才。有人说袁世凯只会夸夸其谈,厚颜无耻,也有人说袁世凯办事认真,不徇私情,机智多谋。一部集兵法谋略、政略宝典为一体的人物大传智慧与杀伐、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81条)
-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有过怎样辉煌的时刻。洋洋百万字的作品展现了一代枭雄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杀伐、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它不仅是上上乘的史学经典,更是兵法谋略、政略宝典。在曲折生动,卷帙浩繁,墨香四溢的巨著中,体味袁世凯那真实的一生……
广告太夸张了。一部历史小说而已,不是我所需要的对袁世凯的品传,买错了。还好是活动打折买的,价格还便宜。可以看看。 - 看看这个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人要名流千史不容易,一个人要遗臭万年也不容易,对袁世凯最多地认识是来自历史书上的一些事件,正史野史都要看,才可以客观的看待这样的人物
- 历史大家写的书,不一样的袁世凯,这三部是剧本式的比较生动,还有一部袁世凯传,也是侯先生写的,唐德刚都推荐了,确实值得一看
- 袁世凯三部曲(全三册
- 袁世凯一生的描写
- 一分为二看袁世凯
- 袁是中国最落后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只有在中国这个社会才能如鱼得水!
- 最为封建王朝和民国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应该用多方面进行了解
- 历史怎么写,不重要,况且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去看,一个小人物能变成大人物,一定有他的可取之处
- 买这部书,是为了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书刚开始看,从目前的感受看,这一目的会达到。
- 全面了解袁公的一生,客观的去评论是非成败
- 不是共产党员,肯定想当皇帝。中国特色吗!
- 下了订单,没收到货。
- 真正的历史学家能以客观的态度去写书而不夹杂历史阶级观此书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强烈推荐
- 最近喜欢读史,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老袁
- 历史小说,随便看看
- 书的质量一般 内容还没来得及看
- 这套书蛮新的,没有塑封的,用编织带捆着的
- 书很轻 质量好
- 帮朋友买的,朋友很喜欢书的质量都非常好满意
- 内容丰富,很不错的书籍。
- 纸张一般,喜欢此类的买来看看,还是可以
- 有兴趣的可以买来看看
- 儿子看得不肯放下。
- 赶上满额减 真是物超所值 赞 好书!
- 小说家言,立场性的东西,不多言
- 还没到手呢,应该不错吧,很期待
- 200减100,太给力了
- 没有那个能力,怎么能够把权力玩转的如此的灵
- 不错的哈 值得一买
- 今天读完侯宜杰先生的《袁世凯》三部曲,这是一部很好的著作。我对清末民初的历史缺乏常识,这本著作对我很有帮助。历史教材的内容是极其贫乏的,充其量只是一本标签簿。但是你朝袁世凯身上贴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后来的人物又超越袁氏多少?大约现在还无法开口评说。侯先生著作的好,就在于他把袁氏当作一个人来写,而不是当作一个国贼来写。他写了一个人,是如何变成国贼的。侯先生写出了人性。一、做皇帝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当然很多人会否认这个说法,我认为这只是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潜意识。袁世凯想称帝,其实和成龙大哥偷吃一样,无非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么,为什么袁氏想当皇帝,会被世人痛骂呢?因为时代改变,而袁氏对此漠然不知。清帝退位,国家整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这说明什么?说明了由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法律定义,已经失效了。共和制要求的是一群人分享权力,进而形成相互的制约,以保证个人权利的回归和完整。换句话说:你还能不能梦想当一个皇帝呢?能!当然能。不仅能梦想,而且也可以实现,那就是你做你自己的皇帝,但不要去做别人的皇帝。而别人呢,也不来做你的皇帝。袁氏是聪明人,可惜他没有真正地为自己着想。他不知道他只能做自己的皇帝,他想赌一把,来证明皇帝梦是可以成真的。结果,他把自己变成了梦想的祭品。二、历史总是兵食优先于信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信是第一位的,兵和食(军事和经济)可以往后放。但是历史的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军事和经济总是最重要的。而军事和经济的颓废,才是推动政治改革、文化改良的动力。兵不胜,食不饱,才会去看看信的东西对不对?要不要调整一下信什么?清末正是如此。列强的军事打击使君主的威信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而经济的衰败又促成了最基层的信念摧毁。大家总是说现在是一个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时代,其实这没什么不好,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没有那些列强来敲打敲打,我们现在很可能还是拖着辫子、套着袍子呢。信仰缺失,要看缺失的是什么信仰。如果是对身外之物的信仰,那么缺失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旧的观念、信仰被摧毁,所以才能迎来新的时代。军事和经济的失败,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政治体制。亿兆民众围绕一个人的政体,着实荒唐。而生杀予夺之出自一人,也着实恐怖。一个荒诞的政体,即使它被包装得再美妙,可是一经暴露,就再也无法恢复自身的神话了。君主政体的终结正是如此,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即使偶尔曲折,但总是向前迈进。三、依赖外力支持的政体是无法持久的封建政体依赖什么?我认为它依赖的是等级制度,和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分权、分享。君主制依赖什么?我认为它依赖的是专制。且不说从等级制度过渡到专权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而是专制到了这一步:集举国之权于一人,还难向哪里发展?物极必反,集权必然走向分权。袁氏政体所依赖的根本是北洋军队。其实质是一个军事团体内的分权、分享。假托共和政体,这种分权和分享得以延续。可一旦重回君主制,则分权和分享就无从谈起了。这是袁氏称帝而众叛亲离的原因所在。凡不能由政体内部自己产生发展的力量,而须依赖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来加以维持的政体,是不能长久的。你可以选择停滞,甚至倒退。可是历史的力量总是向前、向前,它会推着你不断地向前。共和,作为一个政体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已经生根,但尚未落实。我们必须经历一系列的曲折,然后才能达致共和的成功。所谓走向共和,但我们尚未走到。&n
- 正向作者在后记当中说的,现在老百姓接收正史更多的是从演艺、电视剧等方式获得,这样的方式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所以,作者也采用了文学写作的手法;但文学写作允许虚构而作者又不脱离真实历史,力求给读者展示那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平时上班也没多少时间看,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细细品读。终于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阅读完作者的心血之作。我认为袁世凯生逢乱世,奸诈、精于权术;文化不高,但懂得驾驭人,为自己所用;重感情,对于各种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惜重金、高位、甚至联姻等方式笼络;有野心更有魄力、也有地痞流氓之性,说话出尔反尔。总之,生在那个动乱年代,早就了一批英雄人物,也出来了一批乱世枭雄。我想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吧。 - 对于那些想知道一百年前的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最好从袁世凯这个人入手,而要想很快地了解袁世凯这个人,最快的办法还是读侯宜杰先生的这部大作,虽然有的地方,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 感觉较为完整的叙述了乱世枭雄袁世凯的一生。印刷也不错。
- 这套书很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的一生
- 看看袁世凯,看看晚清,看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看了一章,还不错,就是不知会不会美化袁世凯,有待进一步阅读。
- 作者写书感情色彩过浓,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写文章
- 书是买来老公看的,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没读过所以无法对内容进行评价,但是书的质量很好,也是在书店看好后再来当当的,性价比高。
- 真正的了解下
- 书的内容还行。但是包是样品。当当自己后加工的。期中一本明显跟其他颜色不一样,封面都泛黄了。但不影响阅读。凑合看了
- 三本,超厚,当当有点不厚道,书的封面和封底都有破损
哎,当当你以后可别忽悠我们这样的金卡会员了 - 写得比较真实,全面,好
- 内容没看,书还行
- 未读,书印刷质量还可以
- 刚看完,不好也不坏
- 我是我喜欢的那种,小说的形式,休闲的时候看吧
- 应该不错吧,了解一下袁大头
- 有不少启示,谢谢作者。
- 事非功过可能还耍再过几十年才能定论。
- 质量好值得价位也可以
- 印刷很好,内容也不错。
- 内容还没有来得及看,但是可以全面看看封建帝国最后的奸雄全貌吧!
- 情节平淡,出场人物众多,但偏于脸谱化。
唯一值得赞扬的是,作者对清末民国初的历史典籍应该有不浅的研究。
譬如,袁世凯究竟算不算真正的做了皇帝呢?因为,他在国内只是简单的举行了个所谓的仪式,在国际上却始终用的是中华民国的名义,而且列强也从未对袁的中华帝国予以承认。
综合看下来,对于人物传记类的历史著作,近三十年仍然未见到能超高阳先生的《胡雪岩》与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 - 袁世凯是个奸臣贼子,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恢复帝制,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学到的。不过后来我知道,历史书是假的、断章取义之后,不再相信。估计袁世凯也不一定是那个样子。本书能让你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的书写角度不同,看人也不会那么死板。
- 感觉一般般,只有袁世凯,周边的一切大事都没有。
- 三部曲中的一本裁剪不好,边角上还有碎纸的突起,而且不知道当当的仓库是不是整洁,书有点脏,都是土;内容没得说,很好!但是建议书籍保持干净。
- 怎么说呢,资料占有蛮详细的,但还是不能与唐浩明的《曾国藩》相媲美,不管是文笔还是心理描写、历史细节处理等等。
- 价格便宜的买来再说,放着慢慢看
- 内容不错,就是作者措辞上不是很好,感觉有些明显与人物不符,可人家毕竟不是专业作家,文章在组织衔接时过于僵硬,有种堆砌的感觉,看久了容易疲惫,缺乏一些小说的可读性
- 从另个角度了解历史人物。
- 看这套书的同时,在网上正好买了《走向共和》的碟子看,一口气看完,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印象。
- 就是书的质量纸张不太好
- 特价一套近30入手的,质量一般,比盗版的好不了多少,看来是一分钱一分货。以后还是不能捡便宜啊。30元我可以买一本精装书还有多了。
就当是街边摊买的盗版书,随手翻翻,翻完扔掉即可。倒是为搬家的时候省了不少负担。 - 但是勉强可以看一看,小说之言
- 袁总在朝鲜捣过浆糊啊
哈哈 - 特价购入,值
- 内容丰富,但过于琐碎,芝麻大的事都拿出来讲,浪费时间。
- 了不起
- 包装完好,内容不错,可以一睹!
- 挺不错的,很有收益;只是写法太小说化了。
- 原来以为是史书类,看见书后才知道是小说演义类。已过了看此类书的阶段了。
- 该作者的文笔和对人物的描述比一个普通的初中生都不如,见过差劲的,没见过这么差劲的!
完全看不下去,想丢掉。 - 做为通俗小说来看还行。
- 什么垃圾书,一点水平都没有。
- 卓越删帖了,真的好可恶买盗版书还不让人说
- 几点问题:1.连个前言,序都没有2.纸质太差3.有点偏向于小说的性质而非史实类记载
- 作者从宣传历史真实的角度写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个历史中的袁世凯。虽然其中不乏作者眼中的袁世凯,但总得来说,还是客观公正的。非常精彩!
- 这就是我一直在卓越买的原因
- 书不错,再打点折就好了
- 此书纸张可不是一般的粗糙啊,要是蚂蚁在上面爬一会儿,能把脚一直磨掉到大腿根,和我在盗版书摊上花10元钱就买一大厚本的书的纸张不堪伯仲,这样的纸张还卖这样的价钱,贪得无厌昧良心的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