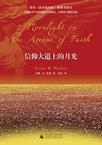信仰大道上的月光
出版时间:2009年6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吉娜•B.那海(Gina B. Nahai) 页数:350 字数:200000 译者:邱仪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中东地区底层家族命运跌宕的故事。来自贫民窟的美女罗仙娜在夫家遭遇了爱情的困扰,与公公不熄的恋情成为悲剧的火线,五岁的女儿莉莉亲眼目睹了母亲罗仙娜从位于信仰大道的家里的阳台上纵身跃下。作为目睹罗仙娜消失的唯一证人,莉莉在此后的十三年里孜孜以求,寻找母亲的下落,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想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让我们追随着罗仙娜踏入这一精彩的传奇,这个出生在德黑兰犹太人贫民窟里的“不吉利的孩子”,从伊朗君主制的奢华世界,进而来到土耳其的妓院,最后到了洛杉矶这一“流亡之城”,并在那儿与莉莉重逢。作品有如伊朗女性版的《追风筝的人》,写中东的颠沛流离,犹太族裔的苦难记忆,政局的更迭和宗教的冲突,以及新世界带来的希望。作品格局壮阔,笔触富丽,却又私密动人。
作者简介
吉娜•B.那海(Gina B. Nahai)
出生于伊朗,从小在社会的底层与中层之间流动,满眼都是社会与人生的创痕,后在美国和瑞士接受高等教育,当代西方最有实力的小说作家。代表作《孔雀哀鸣》(Cry of the Peacock)、《信仰大道上的月光》(Moonlight on the Avenue of Faith)等问世,风行全球,令整个西方世界文坛大开眼界,一些评论家将之媲美于马尔克斯。曾负责为美国国防部研究伊朗政治,经常就伊朗犹太人历史和流亡主题发表演讲。目前,那海女士与家人居住在洛杉矶,并在南加州大学教授小说写作。
章节摘录
我望着她,重达三百九十三磅,而且还在与日俱增。她身形庞大,以至于两个多月来都没站直过,进门如不先把门框卸下来就挤不进去;她的喘息如此粗重,使得目前她和姐姐在洛杉矶住的那条街的狗狂吠不止,使得夜半时分隔壁邻居弹奏的钢琴曲都变味走调了。很难想象我的母亲,“天使”罗仙娜,从前是个目光流转、肤如凝脂的美丽女子,一声娇笑,整个世界都会戛然而止。弄得男人们,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神魂颠倒,从城这头追到城那头,也搞不清为什么要追她,如果她真停下来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恐怕都会不知所措。她精致小巧,仿佛地球引力、人生苦难也奈何她不得。一个漆黑如梦的夜晚,她长出双翼,振翅飞向伊朗群星璀璨的夜空,夜吞没了她。那时候,整个德黑兰市都被罗仙娜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我的父亲,爱她胜过世上所有人,因此陷入了痛苦中,终其一生不能自拔。而我,在她飞向天空的那一刻其实就在她身后,之后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期盼她的归来中度过。关于她的去向和命运传言四起。我的朋友们怀疑她已经死了,就埋在我们位于信仰大道的家的后院里。他们因她的死责怪我父亲和他的父母。从小把罗仙娜养大的大姐“月姑”米丽亚姆把找到妹妹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即便违背罗仙娜本人的意愿也在所不惜。“天使”罗仙娜一直朝前飞,从不为地球引办所困,也不为亲人们的呼唤所打动,从未停下过脚步回头看看自己离去十三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她从一座城市转到另一座城市,横穿了伊朗和整个土耳其,栖身于没有门牌号的房子和无名的街道,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女子,只剩下犀利的双眸和缓慢流逝的美。几个月前,一种神秘的液体开始毒物般充斥她的身体,从她的眼角慢慢溢出,使她的手脚肿胀得动弹不得,从前梦幻般美妙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呓语,她最终只得停了下来。如果不是这样,她恐怕永远也不会停下脚步,也不会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找到她。母亲离开时我只有五岁,回来时我已经十八岁了。我的姨妈“月姑”米丽亚姆告诉我要理解罗仙娜的不告而别,她是受了不可知的命运的摆布,抛下我不是她的本意,而是在我出生前几百年间就一直存在的神秘力量作祟的结果。米丽亚姆说早在罗仙娜为人妻为人母前,早在她来到人世前,甚至被怀上前,就注定要离开了。现实世界就是如此,米丽亚姆告诉我,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不过是残暴命运手中的器物,自由意志、自作主张都只是心灵的兴致所至,脆弱得经不起荒谬的生存现实的打击。因此,她说,我必须原谅罗仙娜,原谅她的不告而别,原谅她听到了我的呼唤却从不应答。我必须原谅她,因为离开我和我父亲对她来说,所承受的打击比我们这些人都更残酷。米丽亚姆坚持认为,哪怕基于信念我也应该这么做,因为虽然现在她回来了,就躺在“月姑”米丽亚姆位于西洛杉矶老兵大道的家里的一间空余卧室里,虽然她看着我,因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变得暗淡无光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但“天使”罗仙娜仍然拒绝作出一言半语的解释。“月姑”米丽亚姆告诉了我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故事。贫民窟1938年她出生于1938年,是“美人”淑莎和裁缝——人称“尺子”拉曼——的女儿。她家住在从淑莎母亲——可怖吓人的碧碧——那儿租来的两间房子里。老太太在德黑兰犹太人聚居的贫民窟里有三幢房子,一间一间地租给了那些找不到别的房子只能忍受她无理要求和苛刻条件的住户。碧碧对女儿也不例外,贫民窟里很多人私下里都在传,说她从未免除过淑莎哪怕是一个星期的房租。干打垒的房子没铺毯子,也没窗户,随便找来几块木板钉在一起,便成了歪歪斜斜、吱呀作响的窄门,门通向院子。第一间是淑莎和丈夫的卧室,白天就成了他做衣服的地方;第二间是家里的饭厅和客厅,兼做孩子们的卧室。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睡在地上——五个小身子挤在一床被子里,手脚交错,肌肤相亲,早已熟悉了彼此身体所带来的温暖,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在床上睡,都是睡不着的。在罗仙娜三岁时有一次她被一股奇怪的气味弄醒了。泥地上铺了薄薄的帆布毡子,毡子上是布单,她就坐在布单上,这是能把她与泥地里到处乱爬的虫子隔开来的唯一东西。她很小很瘦,动作轻巧,从不会惊扰到任何人。她探过身,叫醒了米丽亚姆。“我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她说。米丽亚姆叹了口气,翻过身去。她九岁了,打小就照看年幼的弟妹。“是不是哪儿疼?”她闭着眼问。“不是,不过我的腿没知觉了。”米丽亚姆摸了摸罗仙娜的前额。“你没发烧呀,”她断定,“快接着睡。”一个小时后,米丽亚姆醒来,吓坏了。只见罗仙娜仍睡在老地方,别的孩子也在熟睡,但是她感觉到房间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闻惯了的皮肤和头发的味道,也不是剩饭剩菜、旧衣服或是干燥贫瘠的土地的味道,“月姑”米丽亚姆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她点燃蜡烛,四处打量,没有物品挪动的痕迹。她又看了一下罗仙娜,她的头发湿漉漉的,双臂张开,浸没在一地的白色羽毛中。当时罗仙娜看起来是那么平静美丽,沉浸在充满遥远群山和湛蓝大海的梦境里,米丽亚姆都担心如果有谁此刻唤醒她,她可能会死去。于是她挨着她躺了下来,躺在那一地自得在月光下看起来几乎成了蓝色的羽毛上,希望也做个跟她一模一样的梦。之后米丽亚姆又多次看到过羽毛,经常闻到离城千里之外的里海的气息,有好几个夜晚她甚至担心罗仙娜会淹死。她害怕如果有人发现了那些羽毛,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便把羽毛藏到了被子里。她用手指把被子撕开一条缝,把羽毛塞在因年深月久而变薄发黄的棉胎上。不过一段时间之后,罗仙娜的秘密就沉重到她再也无法一人承受了。一次,房间里的空气湿润得结成了水滴,从屋顶上大滴大滴地滴落到孩子们的脸上和头发上。米丽亚姆去叫来了母亲。淑莎光着脚,睡眼惺忪地进来了,披巾松松垮垮地围在腰上。她站在罗仙娜身旁好一阵都没注意到羽毛的存在。“你看!”米丽亚姆抓起一把羽毛,凑到淑莎眼前,“好几个晚上我一觉醒来,就在她身下发现了这些东西。”淑莎倒吸一口冷气,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她的身体晃动了一下,虽只一下,其力道却足以使米丽亚姆赶紧闪开,以免被碰倒。她看见血色从淑莎身上退去,皮肤仿佛变得透明起来。“还有谁知道这事?”淑莎问。“没别人。”米丽亚姆真希望自己当初没叫她来,“我把羽毛都藏起来了。我肯定不会有人知道的。”正在这时,达拉亚特,淑莎的二女儿,在睡梦中动了一下。她用手抹着脖子和胸口上的汗,同时对梦中情人含混不清地嘟哝了几句。她不过八岁,从未与家人之外的男人有过任何接触。但早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已经被欲望——一种她成年后也无法摆脱的原始的、永不妥协的激情所攫住了。淑莎把目光从达拉亚特身上移开,朝外走去。她坐在卧室通往后院的台阶上,然后示意米丽亚姆过来坐在她旁边。她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子——黝黑的肌肤,黝黑的眸子,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美。任何见过她除下面罩后样子的人,都觉得她给人一种不可思议和忧伤的感觉。而她却对自己的美浑然不觉,或羞于提起。“你不能跟任何人提起羽毛的事,明白吗?”她问米丽亚姆。.米丽亚姆点了点头。“你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吗?”米丽亚姆刚开了个头,就突然停住了。两人笼罩在一片静寂里。一千年来,秘密像一张大网,铺撒开来,人们对说出口的话所具有的力量的敬畏和其后果的恐惧让这张网越张越大。所以米丽亚姆停住了口,而淑莎也没告诉她自己最清楚不过的答案:罗仙娜身下的那些羽毛其实就来自她自己的梦境,在梦里罗仙娜如鸟儿或天使般飞翔,越过浩瀚无垠的大海,飞出贫民窟那把守严密的边界。有时双翼和海风溢出了夜的边界,忽略了愿望和真实的界限,涌到罗仙娜的床前,道出了她内心的渴望。
媒体关注与评论
优美,丰富,充满异国情调……我们跳上了一张魔毯,在信仰大道上呼啸而过,心满意足地由着这位故事高手编织其魔法。 ——《波士顿环球报》让人着迷……一个永远不偏不倚,把愤世嫉俗与希望,热情与讽刺,生活的重压与飞升的欣快平衡起来的声音。 ——《洛杉矶时报》作为一名技艺高超、充满创造性的作家,那海证明了,即使是最黑暗的魔法也无法击败爱的神奇力量。 ——《纽约时报书评》
编辑推荐
《信仰大道上的月光》:荣登《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榜首,全球30多个国家地区引进版权,19种语言翻译出版。
名人推荐
伊朗的犹太女性悲歌作者:陈一白(即《追风筝的人》译者李继宏)(《信仰大道上的月光》,[美]吉娜•B.那海著,邱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350页,26.00元) 1991年,年满三十周岁的伊朗裔作家吉娜•B. 那海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孔雀的哭泣》(Cry of the Peacock,Crown),使得美国读者第一次能够通过小说了解波斯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 《孔雀的哭泣》(以下简称《孔雀》)的时间背景是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的1982年,高龄一百一十六岁的女主角孔雀遭到革命卫队的逮捕。在孔雀等待审判期间,她自己和伊朗犹太人的故事,被吉娜•B. 那海极具感染力的文笔编织成一张绚丽斑斓的波斯地毯,其上不但呈现了伊斯法罕的犹太人隔离区的风情,也描绘了孔雀自九岁开始与宫廷歌手所罗门的婚姻生活,更回溯到两百年之前的1796年,借由第三人称叙述了孔雀的高祖父母酿酒商约瑟夫和占卜师依斯特对后世的先见之明。 许多作家的文字风格和题材偏好从其处女作便露出了恒久不变的端倪,那海的情况也是如此。《孔雀》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文风和伊朗犹太人题材,在作者后续的作品中反复地出现,尤其是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信仰大道上的月光》(Moonlight on the Avenue of Faith,Harcourt,1999)中。 《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以下简称《月光》)和《孔雀》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也是发生在伊朗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尽管城市从伊斯法罕变成了德黑兰),也是以离经叛道的女人为主角,也是将个人、家族和种族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是大量地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如果套用计算机软件的术语,我们可以把《月光》当作《孔雀》的升级版。 《月光》中的主角并不是“我”(莉莉)。莉莉只是个拥有全知视角的叙事者,她要讲述的是她母亲罗仙娜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头,曾经风情万种的罗仙娜已经命悬一线,“重达三百九十三磅,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第3页)。莉莉告诉读者,这两种状态之间相隔十三年,“母亲离开时我只有五岁,回来时我已经十八岁了”(第4页)。由于罗仙娜病入膏肓,口不能言,于是莉莉的姨妈米丽亚姆“告诉了我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故事”(第4页)。 罗仙娜1938年出生于德黑兰的犹太人隔离区。罗仙娜的家族每一代都有女性成员离家出走,因而“被人另眼相看、鄙视唾弃”(第12页)。她的外婆碧碧对这样的污名深恶痛绝,所以守寡多年的她对罗仙娜的母亲淑莎严加管教,生怕悲惨的历史再度重演。淑莎谨守妇道,生下了六个子女,其中包括了米丽亚姆和罗仙娜。 罗仙娜出世时,犹太人隔离区出现了异常的天象,“太阳晚升起了十四个小时”,所以许多人认为她的诞生是个恶兆,尤其是她的外婆碧碧和她的母亲淑莎。淑莎亲眼见证了罗仙娜在成长过程中造成的种种怪状(比如说睡觉时身边会出现羽毛和里海的味道)和带来的厄运(让家里人染上天花),决意亲手把她杀死,找了个机会把她推下屋顶。罗仙娜并没有摔死,而是第一次飞起来,魔幻地失踪了五个小时,然后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罗仙娜的第二次飞翔是在二十八年之后的1971年。当时三十三岁的她已经度过了十年的女佣生涯(八岁那年被父母送到富婆亚历山大家当佣人)和十五年痛苦多过快乐的婚姻生活,不堪各种心灵和肉体束缚的罗仙娜狠心抛弃女儿莉莉和身为伊朗皇室后代的丈夫索拉,逃离了婆婆佛罗兰•克劳德的严密监管,神秘地出现在离她丈夫家“好几英里之外的卡哈伊河”(第161页)。 罗仙娜并没有获得她渴求的自由,而是沦落到土耳其边境的妓院出卖肉体,历尽千辛万苦脱离魔窟之后,立刻又陷入日常生活的艰辛,风华绝代最终被滥交和贫困折磨得“苍白瘦小、脸上布满皱纹,皮肤干燥,紧紧绷在尽是骨头的脸上……手干裂且黑”(第285页)。 失去母亲的莉莉紧接着又失去了父亲:索拉安排她独自前往美国求学。莉莉在异乡得到罗仙娜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女儿默西迪丝的资助,顺利地度过了孤独而平静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而在她的祖国伊朗,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那富可敌国的祖父铁木尔被逮捕,家产均被充公。但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三载之后的1978年,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被推翻,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回国后主持了公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度,改国号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莉莉的父亲锒铛入狱,一代豪门终于烟消云散;反倒是她的几个姨妈和舅父顺利逃到了美国,最终得以和她团聚。 接下来的故事乏善可陈,米丽亚姆偶然获悉罗仙娜在土耳其出现,于是前往该国,为罗仙娜制造了进入美国的机会。走投无路、心怀愧疚的罗仙娜最终来到了美国,却病倒在街头,等莉莉见到她时,她业已生命垂危,出现了本书开头的一幕…… 理解《月光》的关键是书中的两个紧密相关的意象:犹太人隔离区和罗仙娜的飞翔。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犹太人在两千年的大流散中,遭到了罄竹难书的剥削和迫害。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他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过着如同过街老鼠般的生活。直到中世纪末期,犹太人没有固定聚居区的历史才告终结。1516年,以海上贸易而繁荣的威尼斯率先展示出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城区设立了专供犹太人居住的隔离区,当年的威尼斯语称之为Ghetto。尽管如此,信奉正统天主教的威尼斯当局也不可能赋予这个根据《圣经》记载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的民族太多的权利。居住在隔离区的犹太人必须缴纳很高的赋税;每到天黑,隔离区的大门便会关闭,禁止犹太人外出活动。 自此之后,欧亚各地相继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掌权的当局对它的管理大同小异。《月光》中的德黑兰犹太人隔离区并不例外,它有许多隔开犹太人居住区和外部世界的大门,比如为罗仙娜接生的紫娃的家就“位于贫民窟第七大门附近”(第20页;简体中文版不知何故把Ghetto翻译成它后来的派生义项“贫民窟”);直到二战将近结束的1943年,被盟军占领的伊朗才颁布了新法律,“允许犹太人搬出贫民窟去居住”(第27页)。 居住在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即使循规蹈矩,也未必能够苟且偷生,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十九世纪上半叶,伊拉克的巴格达和波斯(即今伊朗)的马什哈德都曾发生过犹太人遭到集体屠杀的惨案。这样的事情到二十世纪仍然时有发生,摩洛哥、也门、利比亚、伊拉克等地均有犹太人冤死的例子。对于犹太人来说,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了隔离区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逃出隔离区、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集体梦想。 而对于犹太女性而言,逃出隔离区还有另外一层更为复杂的含义:除了遭到种族外部的社会隔离,她们还受到种族内部的男权束缚。这也是吉娜•B. 那海在《月光》中所要重点描绘的主题。上文已经介绍过,罗仙娜的家族每一代都有女性成员离家出走,这种魔幻主义的传统始于该家族一位绰号“乌鸦”的女性。“乌鸦”的丈夫是一位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的法师),“拉比对妻子和女儿们严加看管。他把她们裹在一层又一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黑布衣里,不准她们说话,纵有别的女性在场也不成,也从不告诉任何人她们姓甚名谁”(第10页)。经过多年的默默忍受之后,“乌鸦”终于发神经了,赤身裸体地在隔离区里边走边歌唱,来到了连接隔离区和德黑兰市区的大门处,“然后就消失在了赎罪日火辣辣的阳光里……”(第12页)。 那海用荒诞不经的魔幻现实主义描写来对犹太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进行女性主义的控诉。在《月光》中,大多数女性要么充满了过度旺盛的性能量,比如热衷于和性无能的丈夫的侄儿偷情的达拉亚特;要么极度自私而且善于玩弄手段,比如为了嫁给富豪铁木尔而不惜费尽心机把自己伪造成德国人的佛罗兰•克劳德;要么两者兼备,比如通过勾引富人阿明而达到移居美国目标的默西迪丝。被那海委以主要控诉人重任的,则是书中的主角——能够飞翔的罗仙娜。 她的出生被视为不祥之兆,家里发生的倒霉事全都被认为是她引起的,年方五岁就遭到生母的谋害,只有靠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才能逃生。罗仙娜的第一次飞翔使她摆脱了种族内部的家庭束缚,最终在八岁那年被父亲拉曼送往有钱人的情妇亚历山大家里当女佣。 在与亚历山大相依为命十年之后,罗仙娜逃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德黑兰市区偶遇了前朝皇室的后代索拉,开始了她在犹太人社群之外的旅途。但过上锦衣玉食生活的罗仙娜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她和索拉的结合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生活的无奈;更为悲哀的是,她真正爱的人竟然是索拉的父亲铁木尔。莉莉出世之后的某天夜里,罗仙娜和铁木尔发生了媾合,随后男权社会的各种禁忌在她周围变成逼仄的铜墙铁壁,令她喘不过气来。于是罗仙娜再次飞翔,利用魔幻主义的力量逃出了伊朗。 实际上,罗仙娜是全体犹太女性的化身。正如吉娜•B. 那海通过米丽亚姆之口所说的:“早在罗仙娜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早在她来到人世前,甚至被怀上前,就注定要离开了。”(第4页)作为叙事技巧,魔幻现实主义的特殊功能在于,它能够通过超越现实的隐喻意象来强化某种文化或社会的现实。在《月光》中,罗仙娜的飞翔所要强化的是:犹太女性遭到的束缚是如此之紧,乃至惟有借助超现实的力量才能摆脱。但是摆脱之后呢?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海是个悲观主义者,她奏响的是一曲伊斯兰世界的犹太女性悲歌,她给出逃之后的罗仙娜安排了凄惨的下场,并且不无悲哀地让米丽亚姆指出:“人类不过是残暴命运手中的器物,自由意志、自作主张都只是心灵的兴致所至,脆弱得经不起荒谬的生存现实的打击。”(第4页) 《月光》是不错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小说。但如果读者想通过阅读这本书,来加深对目前每天占据报纸国际新闻版面头条的伊朗总统大选纠纷的理解,那必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本书所描写的是伊朗犹太人的生活,而伊朗的人口主体是波斯族(51%)、阿塞拜疆族(24%)、吉拉克和马赞德兰族(8%)等民族,波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哈扎拉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加起来,才占到伊朗总人口的1%。《月光》中确实有提及伊朗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变迁,但它对这种社会过程的描写是维基百科式的,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穆萨维如何会从哈梅内伊的左臂右膀走到他的政见的对立面。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对伊斯兰世界的浓厚兴趣已经延伸到文学领域,应运而生的是许许多多描写中东地区的作品。这些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兜售异国风情为主、本质上和欧美文学传统血脉相连的作品,比如哈立德•侯塞尼那两部极其畅销的作品;一类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独特的阿拉伯文学传统的作品,比如拉维•哈格的《德尼罗的游戏》(De Niro's Game,Anasi Press,2006)、拉比•阿拉米丁的《讲古人》(Hakawati,Knopf,2008)和卡德尔•阿卜杜拉的《无字天书》(Spijkerschrift,De Geus,2000)。那海女士的这部《月光》属于前者。虽然出生在伊朗,但她的作品,无论是《月光》之前的《孔雀》,还是《月光》之后的《里海的雨》(Caspian Rain,MacAdam/Cage,2007),都没有显示出阿拉伯文学的痕迹,反倒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莎贝拉•阿连德的影子。 当然,吉娜•B. 那海是个好作家,她的《月光》肯定不会让那些花了二十六块钱人民币的读者感到不值。至于出版方给她戴上的那顶高帽,“当代西方最具实力的小说作家”,若非虚伪的欺骗,便是真诚的无知,那海女士若是知道,恐怕会深深地感到难为情,请把它当成笑话吧。■流浪者之歌——读《信仰大道上的月光》李冬梅我听着“流浪者之歌”看完了《信仰大道上的月光》。音乐反复播放,书每天看几十页。看得酣畅淋漓,如梦似幻,每次只看几十页,不想饕餮地一口气看完。读到最后,不再强忍决堤泪水。看书签上的作家照片,一个美丽性感的中东女子:吉娜□那海。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有关大海、飞翔、自由和魔力的书。它的主人公是一群苦难中做梦求生的女人。她们有太多眼泪了,她们过于沉重,深陷泥淖。然而,那海让信仰生出一双魔力翅膀,赋予主人公片刻飞翔的自由——尽管你分不清那是否一场过于美丽的幻梦,时刻揪心于她的坠落,那信仰的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残酷屈辱的现实。我们抬头仰望,看到倔强的天使眼泪流尽,飞上倾泻如水的湛蓝天空。这种战胜命运魔法、令囚徒升空的信仰,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它的名字叫自由。故事背景是伊朗德黑兰的贫民窟。在女性只能做套中人、只被允许露出双眼的中东,谈论自由,尤其谈论女性的自由,是件奢侈而大胆的事情。伊朗裔美国女作家那海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作为一名移民作家,一名亲历战乱与禁锢的苦难伤痛、深知“机遇与选择之地”的自由滋味的“离散”作家,那海史诗般的叙述充满着苦难的泪水,却始终不让它们随意倾泻;她讲述的这个堪称女性《百年孤独》的传奇故事,给人更多的是欢笑、惊奇和梦想的轻逸之美,沉郁的语调,辛辣的语言,光怪陆离的事态百相,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处处隐现着苦中作乐的“含泪微笑”。也正因其不控诉、不悲泣的潇洒姿态,这个故事有了更为坚韧强大、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人起敬。《信仰大道上的月光》是一部中东女性命运苦难史,因信仰而得救的跌宕传奇,阴郁的童话,伤口流血的寓言。和《一千零一夜》一样,它是一个圆环状的故事。读开头一章,一头雾水,还以为是个离奇的幻想小说。直至最后一章,它引领读者重新回到最初,才明白它是一支欢畅的哀歌,伤恸的欢乐颂。故事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家族女祖先“乌鸦”被丈夫禁锢,只准露出双眼,坊间盛传其丑陋无比,直到“乌鸦”被生生逼疯,在众人面前袒身露体,艳惊四座。从此,这个家族的女性都仿佛受到命运诅咒,千方百计掩藏美貌,只为保有清白名声,却每每事与愿违,阴差阳错地成为千夫所指的荡妇淫娃。主人公罗仙娜透明如海洋,轻盈如梦境,天真似孩童,欢笑如樱桃花,行路仿佛不受地球引力束缚,睡觉时从梦境中散发出海洋气味,生出片片羽毛,有“天使”之称。年幼时,母亲视她为不祥之物,唯恐为家族带来灾难,推她下楼,她却生出一双洁白翅膀,在德黑兰的夜空中飞翔了足足五个钟头。为寻找出走的童年伴侣,她独自踏上冒险旅途,却偶遇富贵人家,结婚生女,卷入一场泥足深陷的悖德爱情。为了拯救家庭,也为自救,罗仙娜撇下年幼的女儿,再次飞走,展开她自我流放的苦难旅程。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可怜的女儿莉莉。她被父亲送到美国,有严重的自闭症抑郁症和自虐倾向,在对母亲的爱与恨中苦苦煎熬。在这个故事中,她印证了母亲的预言——她“将体验一千次生命,让每一次生命都没有缺憾”。罗仙娜的姐姐“月姑”米丽亚姆,同样有着惊人美貌,却懂得求生之道,早早学会扮丑扮平庸。这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女性,先后遭遇懦弱无能的丈夫,自杀的母亲,失踪的妹妹,接连惨死的儿女,残酷的暴政,纷乱的战火,行政的延宕,命运的捉弄……所有人生的煎逼都加在这个女人的双肩,她却强忍着扛了下来。她祈祷,她对上帝说:“你还没有打倒我”。她变卖家产,颠沛流离,辗转来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她照料充满敌意的莉莉,忍受她所有叛逆的恶言恶行,竭力打探罗仙娜的下落,全力营救,历尽艰难,最终母女姐妹团圆。如果说罗仙娜是《信仰大道》中的梦想和翅膀,那么,这个向日葵一般的坚毅女性,就是这个故事的现实层面的肩膀和脊梁。故事中有一段,讲罗仙娜出轨,被婆婆囚禁,一夜,她偷偷带女儿夜行,让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绽开着一千朵灯光的夜晚。音乐如水冲刷着她们的耳朵,卖花人撞上耍猴人,花落满地。美丽放荡的妓女穿越大街,呼出香水、烟草味和乳白水汽,引发一场交通混乱。露天游乐场的摩天轮如此接近天空,让罗仙娜吐露出幼年时展翅飞翔的秘密,对女儿讲出肺腑之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忍受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曾经飞过的人无法忍受于泥沼中爬行,如同《樱桃的滋味》中,那个一心自尽的人,突然尝到樱桃的美好滋味,百感交集,痛哭流涕,为了能继续尝到如此滋味,而忍痛呼吸,活了下去。这段华彩乐章出现在行尸走肉般的监禁生活之中,小小的自由倏然闪现,仿佛凿开铁屋,呼吸一口清洌的含雪空气。想起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一双魔力翅膀,可以赋予泥胎凡人多少尊严力量。如此看来,故事梗概写成“女主人公爱上她的公公”就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大讽刺。其实,这是一个男性淡出的女性故事,其中所有的男性、爱情、肉欲,在女性的光辉月华之下都黯然失色,恍如虚设。 “月光”,不就是与阳性的“日光”对立的阴性的温婉冷冽之光么?它没有发热的伟力,却因其清洁单纯而具有使雪花变成雪崩的力量。撇开那些独特的背景,它又可被看做是一本讲述母女关系的书。读它的时候,想起安吉拉□卡特的《明智的孩子》来。卡特写伟大女性,家族历史,母女关系,用的是恣肆语言,轻盈背景。与之相比,那海的故事更显厚重。正如美如幻梦的“天使”罗仙娜因过多的眼泪而变成一头肿胀的鲸那样,《信仰大道》也因绝无仅有的女性苦难而拥有坠向地面的力量。沉重的苦难与自由的信仰,向下的力量与向上的力量,背弃与坚守,泥土与天空,囚笼与羽翼,德黑兰贫民窟与富饶的洛杉矶,所有这些相反的力量始终在角力,它们拼命拉扯着这些了不起的女人们。“有毒药,就有解毒药”,她们选择了流亡:“生存下去的秘诀就是欣然接受流亡的命运,适应它,然后接着前进。不管身后留下什么你都必须朝前走,你一定不能厌倦,不能停下来休息,不能走岔路。埋了孩子继续走,输掉了战争继续走……”继续走,直到最终挣脱命运的魔法,漂洋过海,炼就刀枪不入之身,获得了属于她们自己的魔力。《信仰大道》还让我想起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拉什迪、帕慕克、奈保尔的小说,以及最近红过全球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东背景的故事是猎奇,是奇观,是“异国情调”。在西方,谭恩美和汤婷婷们的中国背景的小说也被视作中东小说的同类。可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它们不仅仅是这些。时代的变迁也许遮蔽了心眼,但只要历史还在血液中流淌传承,我们就无法彻底涤净那些屈辱与苦难,这个故事,也必定会与荒诞而现实的《百年孤独》一般,在中国找到它的回音。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37条)
- 先说文笔。我觉得那海的想象力、以及用文字对事物进行描摹的能力非常强大,几乎不亚于张爱玲和马尔克斯。过瘾!虽然是关于女性、关于泪的故事,但这本书其实并不像好多中国书评说的那样,是什么“一部女性主义的悲歌”。应该说,作者的基调是乐观的,探索是没有穷尽的,就像信仰大道上那透着女性永恒之美的月光——温柔而坚定,温暖而执着。记得徐克的经典电影里边,青蛇在人间走一遭,直至最后尘缘历尽,方识人间苦乐,也终于尝到了泪水的滋味。可在这本书中,身为凡人的罗仙娜始终都无法逃离密实的世俗之网,只能在梦中飞翔到大海上。成年后,她既不愿带走母亲的眼泪瓶,也不愿将痛苦传给下一代,只想憋在自己孤独的心中……于是,泪积成海,让她浮肿到成为怪物。可是我想说:就让泪尽情流出来,又怎样?即使泪积成海,只要头上有月,就有拖引潮汐的力量;月之倒影,不正是那让海充满生命力量、潮汐不止的心吗?的确,这是一部充满中东异域风情的作品,可是真正伟大的人气作品,不是靠猎奇心理取胜,而是靠人类某些共同的主题超越时空的。月,泪,海,这本《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中的女性主题,值得现代社会每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深思。或许大家都过于急着赶路,急于以“匆忙”之名逃避身为女性的“自己”……别忘了全书最后一句话:“回过头去,才有可能明了一切,心地安然。”
- 一片神气的土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拥有的同一片天空女人.....坚强软弱怨恨原谅......当爱情和欲望与道德相触我们该怎样选择?决绝的走下去把命运彻底颠覆让自己迷失在未知的远方或者回头承认错误让自己得到救赎放弃那精彩且残酷的世界正视自己的灵魂"回过头去,才能明了一切,心地安然..."就是这样那海带我们走进了那间房子聆听那故事为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女人流泪或祝福!
- 走在信仰的大道上,我们能看到中东的妇女在越来越自强自立自信
- 平时我们很难了解她们的生活,即使作者现在并不是生活在那里,但也给我们展示了伊朗女性的生活片断吧,庆幸不是那里的女人.
- 我想每本小说都是在讲故事,但是我想每个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世界。我们总是能够在一本小说中了解到什么,有些是我们之前就听说过得经历过的,深深的共鸣让人感动,但是有些却是没有接触过的。那种感动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中东,平民窟,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的世界。但是我想我们会被感动的。
- 虽然是等到看完整本书之后才知道讲什么,但是就是一直不断被吸引着看完了。可以,很有哲理。
- 大学时看的书,一口气读完,语言唯美,想象奇特,又不脱离生活,体现了人性的美
- 非常的好看,写心理的时候很细腻,很值得看
- 5星级的书籍,不需要太多语言
- 一口气读完了~语言很梦幻的一本书,很喜欢~
- 她很开心,这就够了~
- 值得一看再看的书,收藏了!
-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真得值得阅读的一本书,推荐了!
- 书带给我不同的视角,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值得一读。
- 自在..
- 故事本身并不是很吸引人,太悲伤了,但是作者的想象力确实蛮天马行空的!另外,看完最大的感触是原来大家都是笨蛋,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好不容易来一遭,就尽量随心好好活一场嘛,不要背负太多压力,好像生来就是要受苦受难似得!心疼阿!希望莉莉以后可以好好生活!
- 个人感觉,阅读这本书有种脏脏的感觉。。。谈不上喜欢,扼。。。。写得太有幻觉?
- 早就听说大陆和台湾今年要出这个小说,昨天收到书看了一个通宵,这不才刚刚看完,这是我这两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了,翻译的文字也非常好。中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神秘而充满不安与骚乱的世界,这或许是传媒给予我们的印象,读了《月光》,我看到和我们一样诡诞而蜿蜒的人生,如酴醾一样开放的青春与梦想,如昙花一样瞬息即逝的美丽与感动,在无量浮动的世尘之中作家演绎着当代命如刍狗的故事。细腻深入的文字,收放自如的情节安排,很好的享受!
- 有些时候,总是会偶然地发现,原以为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却会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来到身边,曾经定格在电视新闻画面的图像,如今是那么地触手可及。一幅栩栩然的画卷,悄然地展开。关于中东地区,有太多的故事要说,这是怎样的一块神秘的地方?天使与撒旦共舞,富饶与贫穷齐在,有眼泪,有微笑,当然,有的还更多,诸如信仰,生存与死亡。诚如书名所言,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不知道是该欢欣还是感到悲凉。当一地的月光照在信仰的大道上,此时此刻,有谁在悄然走来?走向你,走向我,走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总认为,一本好书,读罢之后,无论是泪水还是欢笑,抑或是激励的感动或沉重的悲凉,但一定都会带来一些什么。如是而言,《信仰大道上的月光》给我带来的则是“一篇读罢头飞雪”。
- 读起来很舒服不过我没有看到太深刻的东西大概是我阅历太浅可惜的是,到了结尾有一种美剧的感觉不过我挺欣赏莉莉的
- 我听着“流浪者之歌”看完了《信仰大道上的月光》。音乐反复播放,书每天看几十页,不想饕餮地一口气看完。读到最后,不再强忍决堤泪水。看书签上的作家照片,一个美丽性感的中东女子:吉娜·那海。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有关大海、飞翔、自由和魔力的书。它的主人公是一群苦难中做梦求生的女人。她们有太多眼泪了,她们过于沉重,深陷泥淖。然而,那海让信仰生出一双魔力翅膀,赋予主人公片刻飞翔的自由——尽管你分不清那是否一场过于美丽的幻梦,时刻揪心于她的坠落,那信仰的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残酷屈辱的现实。我们抬头仰望,看到倔强的天使眼泪流尽,飞上倾泻如水的湛蓝天空。这种战胜命运魔法、令囚徒升空的信仰,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它的名字叫自由。 故事背景是伊朗德黑兰的贫民窟。在女性只能做套中人、只被允许露出双眼的中东,谈论自由,尤其谈论女性的自由,是件奢侈而大胆的事情。伊朗裔美国女作家那海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作为一名移民作家,一名亲历战乱与禁锢的苦难伤痛、深知“机遇与选择之地”的自由滋味的“离散”作家,那海史诗般的叙述充满着苦难的泪水,却始终不让它们随意倾泻;她讲述的这个堪称女性《百年孤独》的传奇故事,给人更多的是欢笑、惊奇和梦想的轻逸之美,沉郁的语调,辛辣的语言,光怪陆离的事态百相,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处处隐现着苦中作乐的“含泪微笑”。也正因其不控诉、不悲泣的潇洒姿态,这个故事有了更为坚韧强大、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人起敬。 《信仰大道上的月光》是一部中东女性命运苦难史,因信仰而得救的跌宕传奇,阴郁的童话,伤口流血的寓言。和《一千零一夜》一样,它是一个圆环状的故事。读开头一章,一头雾水,还以为是个离奇的幻想小说。直至最后一章,它引领读者重新回到最初,才明白它是一支欢畅的哀歌,伤恸的欢乐颂。 主人公罗仙娜透明如海洋,轻盈如梦境,天真似孩童,欢笑如樱桃花,行路仿佛不受地球引力束缚,睡觉时从梦境中散发出海洋气味,生出片片羽毛,有“天使”之称。年幼时,母亲视她为不祥之物,唯恐为家族带来灾难,推她下楼,她却生出一双洁白翅膀,在德黑兰的夜空中飞翔。为寻找出走的童年伴侣,她独自踏上冒险旅途,却偶遇富贵人家,结婚生女,卷入一场泥足深陷的悖德爱情。为了拯救家庭,也为自救,罗仙娜撇下年幼的女儿,再次飞走,展开她自我流放的苦难旅程。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可怜的女儿莉莉。她被父亲送到美国,有严重的自闭症和自虐倾向,在对母亲的爱与恨中苦苦煎熬。她印证了母亲的预言——她“将体验一千次生命,让每一次生命都没有缺憾”。罗仙娜的姐姐“月姑”,同样有着惊人美貌,却懂得求生之道,早早学会扮丑扮平庸。这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女性,先后遭遇懦弱无能的丈夫,自杀的母亲,失踪的妹妹,接连惨死的儿女,残酷的暴政,纷乱的战火,行政的延宕,命运的捉弄……所有人生的煎逼都加在这个女人的双肩,她却强忍着扛了下来。她祈祷,她对上帝说:“你还没有打倒我”。她变卖家产,颠沛流离,辗转来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她照料充满敌意的莉莉,忍受她所有叛逆的恶言恶行,竭力打探罗仙娜的下落,全力营救,历尽艰难,最终母女姐妹团圆。如果说罗仙娜是小说的梦想和翅膀,那么,这个向日葵一般的坚毅女性,就是这个故事的肩膀和脊梁。 故事中有一段,讲罗仙娜出轨,被婆婆囚禁,一夜,她偷偷带女儿夜行,让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绽开着一千朵灯光的夜晚。音乐如水冲刷着她们的耳朵,卖花人撞上耍猴人,花落满地。美丽放荡的妓女穿越大街,呼出香水、烟草味和乳白水汽,引发一场交通混乱。露天游乐场的摩天轮如此接近天空,让罗仙娜吐露出幼年时展翅飞翔的秘密,对女儿讲出肺腑之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忍受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 曾经飞过的人无法忍受于泥沼中爬行,如同《樱桃的滋味》中,那个一心自尽的人,突然尝到樱桃的美好滋味,百感交集,为了能继续尝到如此滋味,而忍痛呼吸,活了下去。这段华彩乐章出现在行尸走肉般的监禁生活之中,小小的自由倏然闪现,仿佛凿开铁屋,呼吸一口清洌的含雪空气。 撇开那些独特的背景,它又可被看做是一本讲述母女关系的书。正如美如幻梦的“天使”罗仙娜因过多的眼泪而变成一头肿胀的鲸那样,《信仰大道》也因绝无仅有的女性苦难而拥有坠向地面的力量。沉重的苦难与自由的信仰,向下的力量与向上的力量,背弃与坚守,泥土与天空,囚笼与羽翼,德黑兰贫民窟与富饶的洛杉矶,所有这些相反的力量始终在角力,拼命拉扯着这些了不起的女人们。“有毒药,就有解毒药”,她们选择了流亡:“生存下去的秘诀就是欣然接受流亡的命运,适应它,然后接着前进。不管身后留下什么你都必须朝前走,你一定不能厌倦,不能停下来休息,不能走岔路。埋了孩子继续走,输掉了战争继续走……”继续走,直到最终挣脱命运的魔法,漂洋过海,炼就刀枪不入之身,获得了属于她们自己的魔力。 阅读更多 ›
- 不好意思··可能是在火车上读的·太仓促了··没有理解结尾的救赎··主要是那个女儿··整本书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 是宿命还是自己编织的囚笼 不得其解很多的事情 她自以为是的选择··以为离开 流浪就是她的命运··可是··她却忘却了一个正常的世界 一个正常的家庭··还有一个女儿在等待··她历尽苦难 却也带给了她亲近的人惩罚···在信仰大道上··她不在会流泪了·从此逃难 做妓女··都是她自我的惩罚··而失去她的人··也被她在信仰大道上 在月光下·盗走了一部分的灵魂
- 还没看完。但是觉得看了一半了,没太吸引自己。所以先放放吧。改天再继续看
- 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听说该书人名很多,但是看完了才返现其实不是这样,一个家族的女性的命运发展,对追求自由。很爱很爱哦,很诱惑。。
- 非常值得买的小说,很想继续看这位作者的小说,可惜没有了~
- 看着看着想起了百年孤独和卡尔维诺的一本书
- 这几年中东题材的小说不少,几乎都买来看过,还是这本和胡塞尼的《风筝》好看。我喜欢看普通人的命运,喜欢有悲悯情怀的作品。
- 买了很久了,也看完很久了。最近才来评价。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推荐了买下的。十分精彩的故事
- 到的货与描述不符,跟本不是一版的!!!
- 从来写不来书评。这一本《信仰大道上的月光》。凌晨读完后掩卷走出来,发现客厅窗台洒进来好大一片月光。原来雨夜也是有月光的,或因中秋么,窗有多大月光就有多大,洒满一地,走进去就好像走进了前世或者来生,月光最神秘了。... 阅读更多
- 收到的书长得与图片差很多,纸质一般,书本还有一种药水的味道
- 初看标题以为是革命故事,其实是类似于《百年孤独》风格的作品,女性视角的作品,引人入胜,是那种可以一晚上读完的书。
- 现在涉及中东地区文化生活的小说很多,这本小说也是,每次看都觉得那些民族总是有一种很神奇神秘的感觉
- 书的内容不错,但是邮来的书是盗版的,和看到的很不一样,字体混乱还有错别字。无奈中……
- 有些像童话,但是把生活描述得又那么现实。很多时候都觉得应该是梦境中的画面。主要是描写该社会背景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主人公与命运的抗争、对自由的向往。即时再黑暗残酷的社会中,爱,都会义无反顾的去温暖人的心灵。
- 这本书真的很无聊。
- 还没看完,语言很好
推荐图书
- 惠特曼诗选
- 女優の肖像
- 人间有情
- 住居空间居住空间residential space
- 神话传说三百篇
- 寓言典故三百篇
- 弗拉菲愚蠢的夏天ScholasticReader 3 Fluffy’s Silly SummerSR3
- 毛茸茸遇见土拨鼠ScholasticReader 3 Fluffy Meets the GroundhogSR3
- MIGHTY SPIDERS厉害的蜘蛛
- HelloReader1 We Love The DirtHR1:我们爱泥土
- HelloReader3 Howl! A Book About WolvesHR3嗷呜!狼之书
- I Love Shadow我喜欢影子
- distribution & shipping center 1物流
- 孤独を生ききる
- 乱来
- 室内设计 娱乐空间INTERIOR WORLD Entertainment space
- Interior world 47 shop室内设计 47 商厦
- 家具和室内灯光设计1interior Furniture & lighting style 1
-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基础教程
- 我和蝙蝠一起生活的日子WHEN I LIVED WITH BATS
- 教学作为德性实践
- 办案实用小全书-知识产权办案实用小全书
- 办案实用小全书-公司企业办案实用小全书
- 《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命题点全面解读
- 《房地产估价相关知识》命题点全面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