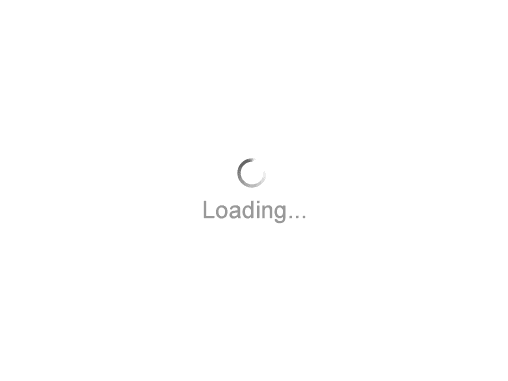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出版时间:1998年5月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黄宗智
Tag标签:无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读黄宗智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以下简称《清代的法律》)这本书的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从无到有的过程。所谓之无,是指初读之时不知其所云,所谓之有,在于通读之后的畅快淋漓与融会贯通。
冯友兰先生在早年提出的历史方法论中提到了两种历史。一类是“事情之自身”,又可称为“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而另一类是“事情之记述”,又可称之为“写的历史”或者“主观的历史”。以此看来,中法史以及清代法律史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清代法律史自身,另一类是写的清代法律史。历史和清代的法律史是不依赖于知识而存在的,亘古唯一;而写的历史以来人的主体性。严格的说,历史的真实是永不可触及的,所有现存历史都是“写的历史”。
冯友兰先生对于这两种历史之存在的处理对记叙者提出了一个理念:即“写的历史应以信为目的”。“信”既为与客观历史之接近,亦为述者价值观之定位。《清代的法律》卷首总序中提到诉讼案件和司法档案的开放是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制度,而《清代的法律》本身即试图通过诉讼案件和司法档案的整理与分析还原清代民法历史本来的面目,并从此论述清代民法史中司法实践与官方和民间表述之间的背离与差异,进而了解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关系从而揭示深层次的政权组织性质。“古文献的艰深、历史家的主观性、假设的不可验证性”这三点“信”的阻碍,在本书的书写过程中,已经最大限度的克服。应该说,黄宗智先生写活了历史,清代的民法实践的细节与全貌随着纸页的翻动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
《清代的法律》不断论证的中心论点其实只有一点,即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代政府的官方表述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也即“实践”与“表达”的背离。
《清代的法律》重版代序部分对全书的概貌做了大致的梳理。
清政府从统治思想上讲,是本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的。在人民面前是摆着法家严肃面孔的。君主总揽大权从而人民没有独立于君权的权利。而在第八章从县官“手册”看清代民事调判的一章也重新提到了清代的县官们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法律制度以及他们的角色的。其中第一层便是手册中仁治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提到政治的好坏,取决于地方官吏,因为“州县理则天下理”。凡事读书之人都晓然于胸的《大学》卷首语中所揭示的读书之用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致最终的理想是“仁”治。而“仁治”重要的一点就是“亲民”,其行为表现即为“听讼”。儒家的意识形态要求官员们让民众信守有德行的人不会堕落到兴讼的地步。这也就意味着清代法律官方的表达是:县官既然是仁者君子,地方政治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确实可能是县官不仁,但县官有儒家教条的束缚,所以更可能的是胥吏不好,鱼肉人民。《大清律例》认为仁人君子本着儒家让人的精神,是不会与人相争的,更不会上法庭;执行仁政的县官,更是会感化子民是他们不会涉讼。所以民众上法庭就归责于不道德的小人。即“讼师”“讼棍”和“衙蠹”。
但真正清代法律的实践并不是这样。作者用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与量化分析结合考察了清代民法运作的实际情况。
第三章处理纠纷的非正式系统:共产党革命前华北农村的民间调解,作者介绍了民间调解的类型、方式、涉及的内容和原则等。贯穿在全书的几章的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特点总是遵从于从实际史料定位及量化分析延展,根据具体案例的呈现说明某一局部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和涉及的解决方式和主客体关系。这里也不例外。作者选择的满铁在华北三村庄沙井、寺北柴和侯家营的调查辅以其他村庄相关的有用资料,从契约、婚姻、债券、继承的案例引入了民间调解的两种类型:由中间人调解的因契约责任引起的纠纷和由组长或社区领袖调解的因家庭和邻里纠纷。论述了民间调解是遵循国法、常识是非和妥协三种原则共同运作的结果,其三个层次结构分别是:隐性冲突;公开纠纷调解和正式诉讼。另外作者也全面的分析了民间调解的弊端和局限:靠民间调解纠正持枪凌弱并非易事。
第四章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大清律例和州县审判中,作者开篇便提出:与民间非正式调解一样,在国家的正式法律系统方面,官方的表达与实际运作之间有许多相悖之处。清代国家对自己的法律制度的表达传达的印象是:其一这种法律制度基本不过问民事;二是即使受理此类案件也往往是凭己意做行政处理或者居间调停,很少利用国家律例。但作者对巴县、宝坻、淡新三地的土地、债务、婚姻、继承案件的罗列,加以引述清律中的户律条文,对应县官断案的具体执行情况,重新展现了清代县官在处理民事纠纷判决的原貌。从其论述上看,其一事实上律例中很多反映实际需要的民事条款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原因是这些条款皆以行政或者刑事的术语呈现,而案例的剖析和具体案例实践才把他们凸显出来;其二从众多案例的分析中,如婚姻案件的审判,没有一件的判决是依照法律外的原则来处理的,而所谓的县官判决的个人主观性,更多是指县官判决中为了保全情面、妥协退让的一面。是其讲究“和为贵”的例证。无论儒家的理想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的是道理、实情、律例三者。而三者之中,法律的地位最高。
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在第五章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有了重新的总括。同时这一章是关键性的一章,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三领域的探索是一个全新概念,是这一领域让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发生交接和互动。作者在系统介绍了清代民事诉讼的几个步骤:最初的告状阶段与县官初步反应;中间阶段的正式堂审之前的衙门、诉讼当事人和可能的调解人之间的接触以及最后的堂审随之的明确裁决指出诉讼开始后官方法律促使民间调解进一步展开,或者可以说是官方介入与民间调解共同合作而形成的特殊民事解决机制。在当代美国,用打官司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是根深蒂固的。而在当代中国与清代类似,很多民事纠纷都是通过司法机关以外的调解加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院来处理。这种解决机制的阐发与后文第九章的马克思韦伯和清代法律及政治制度关于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之不同以及作者对马克思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论观点的反驳与深化做了例证和铺垫。
在全书的最后四章主要介绍了清代民事诉讼的规模和费用,指出这些是人民可以负担的;又解读了县官手册,指出县官手册中体现的县官之理性主义和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而提出了县官思维中的“实用道德主义”即所谓道德主义乃是因为它强调了崇高道德理想的至高无上地位,但又是“实用”的,在处理州县问题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两者的关系虽然紧张,却结合为一个整体。在这几章作者又着重探讨了“讼师”“讼棍”和“衙蠹”。在县官笔记中,其呈现的是与官方二元结构截然不同的现实,他们显示地方衙门大体上是按照惯例性的规则和程序运转的。衙门胥役按照惯例办事,即作为公务员的一面,无疑迥异于官方表达中把他们描述成无恶不作的奸徒的形象。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黄宗智试图用现代西方的学术话语来刻画清法史的特征。他与马克思•韦伯的“实体理性”理论对话。批判了韦伯认为中国法律是反复无常、专横的“卡地法”。黄宗智由“实体理性”引申出:清代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理性”的实践两个相互依赖的矛盾方面的结合。
质疑的一点是,总览全书,似乎作者涉及的观点过于繁杂,如果说全书的主要观点是论证“实践”与“表达”的背离,那么在前章中对民事法律纠纷的三种解决途径的展开似乎与中心论点的论述相背离。作者似乎并没有充分的论证这种独特的诉讼结构与表达和实践背离的原因,而更着重的对历史原貌的回顾和复原。虽然着实让读者窥探其全貌与细节,但细细看来与主题无疑。另外黄宗智承袭了美国学者言必称马克思韦伯的特点,最后的一章着重从理论上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韦伯“实体理性”的论述,某种程度上又略显简单。
总的来说,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确实运用了法社会学的思维将法律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分析,对清代的表达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补充了漏洞。正如“Civil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中提到的”I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overeign the legal order in China, a more useful approach may therefore be to emphasize the fact of judicial enforcement rather than the promulgation of rules or the control of coercion. It is such enforce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at brings into play the legitimate application of coercion, which is a hallmark of law’s special force.”
研究中国法律的权力运作,也许更好的分析方法是强调分析律法实际的实施过程,而不是那些成文法条和权力的控制。这或许是《清代的法律》突出于其他中法史研究的独特之处。
- 大清法律制度的矛盾[1]
——读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略记
《大清律例》作为继承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完整法典,一直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布迪和莫里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中就以清律例为研究对象来描述中华帝国的法律制度。布迪认为中国法制思想起源于战国时的法家,在秦律中得到确认,后经汉代融入儒家“仁政”的理念,后世不断继承、很少突破,清律中即表现出重视刑罚而轻视民事活动的特点[3]。黄宗智作为美籍华裔经济史、法律史学者,充分发挥了西方注重实证研究的优势,从县村的诉讼档案入手,详尽复原了清代(到民国)的社会制度,反驳了一般研究对清法史的认识。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早也指出:“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4]”黄宗智通过对清代四川巴县(1760-1850)、顺天府宝坻县(1810-1900)以及台湾淡水-新竹县(1830-1890)三县的诉讼档案的实证分析,并比较了满铁在民国河北顺义县(1940-1942)所做田野调查,论证了清代的司法实践与法典描述的矛盾。从表达与实践的矛盾中,复原了清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黄宗智认为不能仅凭官方表达,也不能仅凭实际行为来理解清代法律制度,强调系统看待表达与实践,其背离反应出法制的本质。
一般认为清代统治者视民事纠纷为“细事”,在法律中很少调整。清律确实以行政和刑法居多,但是黄宗智认为在诉讼实践中,县官并非几乎从不过问民事,相反民事案件是地方法庭受理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实证中,民事案件占了全部诉讼档案的三分之一(黄宗智,2001)。
清代官方表达遵从儒家思想,提倡“君子无诉讼”,认为良民是不会主动涉入诉讼之中的,并将诉讼归咎于讼师的教唆。黄宗智指出在实践中大多数案件的诉讼主体为普通民众。有学者把民众不愿参与诉讼的原因归为畏怯县衙威严和衙蠹的敲诈勒索。黄宗智比较了小农经济的宝坻-巴县与商品化社会萌芽的淡水-新竹县诉讼档案,得出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后,诉讼当事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作为主体的宗族和地主集团不再轻易畏怯诉讼。民众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提起诉讼,并非是受到讼棍的挑唆。县衙案件累积的根源不在于讼师和讼棍而在于清律本身起源的缺陷:只适用于小农经济社会。
滋贺秀三认为县官断案时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情理法”,更像是一个调停人而非法官(滋贺,1998)。按照儒家的理论,这类事务应主要由社会的道德原则而非法律来解决。黄宗智从县官判案的批词中得出,县官并非如官方表达是“教诲子女的父母官”,而是严格依照清律裁判案件。在此要指出,这并不排除县官也乐于依统治思想要求采用庭外和解。黄宗智把村庄民事纠纷的解决分为三层次:民间调解、审判制度和第三领域调解。认为在第三领域,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发生交接、互动,有大批争端,虽然进入官方审理过程,但在正式堂审前都获得了解决。在社区、宗族调解中,黄宗智认为也体现出了背离和矛盾。在儒家话语中,理是指“天理”而社区调解中则指是非对错的道理;情也非儒家“仁”所指的同情心,而是人情,为了维持过得去的人际关系必须做出的妥协。同时国法并非在民间调解中毫无作用,民众通过诉讼文书的批词对法庭可能判决的猜测,促进了和解。
黄宗智在指出了清代法律制度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和矛盾后,认为实践与表达之间的背离凸显由主观解释和客观实践之间微妙的关系所提出的复杂问题。譬如,《大清律例》中条例繁多,且常附在看似不相干的律文下。这表明清律事实上同时包含操作性的条例和道德化的包装;又譬如,把民事案件看作是由地方官代表皇帝来自行处理的“细事”,阻碍了民法制度的充分细致化和标准化。事实上县官大都依法判案,司法体制却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黄宗智对背离原因的解释是:一方面,县官是皇帝的代理人,在地方行使绝对权力,因而理论上全凭己意做行政处理(居间调停);另一方面,县官处于官僚系统底层,受审查制度约束,依照法律循规蹈矩,才能免于危及仕途。
对黄宗智的独特见地,学界有不少反对意见。以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学者梁治平为代表。滋贺秀三比较了清代中国法文化与近代西方法文化,认为清代司法制度中无作为西欧型审判特征的“确定”这一严格的观念。滋贺认为清代司法审判的“情理”性,县官并非严格依照法律断案(滋贺,1998)。梁治平在清代民法的性质上与黄宗智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存在着各种民事关系,但是未产生出可以称之为“私法”的那部分法律。梁治平将中国法文化看做是一种“礼法文化”,县官处理事案件时关注的不是理清财产关系和维护财产权,而是礼法秩序,使天理人情得到彰显(梁治平,1996)。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黄宗智试图用现代西方的学术话语来刻画清法史的特征。他与马克思·韦伯的“实体理性”理论对话。批判了韦伯认为中国法律是反复无常、专横的“卡地[5]法”。黄宗智由“实体理性”引申出:清代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理性”的实践两个相互依赖的矛盾方面的结合。
自本书第一版问世,黄宗智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贡献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继承了西方在社会科学中注重实证分析和与理论源头对话的特点。同时也难免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对实证资料取得过于乐观。在理论方面,也容易陷于西方经典理论。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法律出版社,1998。
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 本文中“矛盾”系依黄宗智原书为paradox的汉译,初版曾译为悖论。
[2]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美) 德克·布迪, 克拉伦斯·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
[5] 卡地(kadi)一词指的是回教的地方官,韦伯书的英译者使用了不同的拼法,亦作khdio。 - 從標題到開篇不久,作者反復強調其中心論點,即清代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之間存在矛盾,本書即解讀這些矛盾在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中的意義(10、14)。這個矛盾可以概括為“言行不一”,言是法律文本表現的國家意識形態,行是司法實踐。如果按照這一線索,作者探討的應該是法律的執行者如何將法律文本所宣揚的理念付諸司法實踐的問題。然而這一線索似乎未能貫穿全書。相反,全書的第2-4章遵循了另一條線索。
在1993年“公共領域”討論中,黃宗智就提出了中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的問題,本書英文版出版於1996年,此書的討論已經基於此框架。在第二章作者介紹了共產黨執政前中國社會的民法概況,之後則分別就社會(民間調解)和國家(司法審判)兩個層面討論清代民法。
第三章介紹了民間調解的類型,方式,涉及的內容,原則等。民事案件主要包括債權、財產、繼承、婚姻。民間調解則遵循國法、常識是非、妥協三種原則共同運作。最後總結了民間調解的性質和運作的三個層級結構:隱性沖突( 支配/屈從);公開糾紛(調解);正式訴訟(訴訟)(73 )。
第四章介紹官方審判,也就是代表國家的律例和州縣審判。 此部分行文基本都是引述清律中的戶律條文,對應縣官斷案的具體執行情況,敘述清代縣官處理民事糾紛的判決。指出縣官依法斷案,並不調停。在本部分的結尾作者略談及律例的差異,前者更代表表達,而後者更代表實踐。作者指出Bodde and Morris已經注意到法律文本與實踐之間的差距(見Law in Imperial China第三部分),但由於沒有地方案件文獻,故未能深入探討這一問題。
本書的關鍵在第五章,即民事調解與官方審判之間的第三領域。作者介紹了清代民事訴訟的幾個步驟,指出訴訟開始後官方法律促使民間調解進一步展開,也就是調解與審判共同合作而形成的解決民事問題的機制。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作者與這種論述模式試圖解釋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不同於西方的特征。
然而,這與全書主題──“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是什麼呢?在11頁,作者先談了“民法的官方表達與實踐”之間的矛盾,繼而稱這種矛盾延伸到民間調解。問題在於:法律的表達與實踐問題涉及的主體應該是執法者,即縣級政府。這種法律領域的矛盾如何與民間調解結合在一起呢?如果能結合,那麼作者談的民法究竟是什麼意義上的民法呢?是“戶律”,縣官“手冊”,還是民間對justice的常識性理解?
也許,一種解讀方式是“表達”代表著國家的話語機制,而“實踐”則是這種話語轉換為行動時的妥協的產物。總之──這部分乍看很清晰,但是放在全書的論述中卻似乎存在邏輯問題。
基於上述法律糾紛解決的第三領域,作者總結了清代民事訴訟的兩種類型: 即小農社會的模型和日益商業化的社會的模型,並認為清代民事法律只適合前者,由於民事審判中很少用刑,訴訟方在訟棍的支持下大膽興訟,誣告,使得法律審判不堪其負。其原因在於商品化和人口增長帶來的日益增多的土地和借貸交易( 160)。
在最後部分本書介紹了清代民事訴訟的規模和費用,指出這是農民可以負擔的;解讀了清代的縣官手冊,指出其理想主義和現實實踐的矛盾, 總結了清代民法“道德主義的實用主義”的特點;最後參照韋伯對法律的論述探討了中國法律的特點。
在後面四章,作者似乎回到了全書的主題,從訴訟程序、費用、規模,法律手冊等更切近民法的具體方面探討了表達與實踐問題。然而,作者似乎太急於構建宏大的對於中國古代法律問題的框架性讀解,從而用國家/社會及第三領域的模式沖淡了表達/實踐的主題。其結果:全書提到很多非常重要的觀點,但是更像論文集,或者可以分為至少兩本書出版。
在序言中,作者稱法律史研究是社會經濟史與文化史相融合的一個角度──這一誘人的宣言結果如何呢?思想與制度如何在法律事件中體現呢?或者說,作者所謂的意識形態的表述與實踐的差異是否一種研究路向呢?其學生Sommer通過性別管理與法律檔案探討國家意識形態、性別與社會史具體問題,也許可以看作融合思想與實踐的一種嘗試。然而法律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進入古代社會文化的道路,這還是有待開發的。
- 像是学术论文
学法律的呢? - 哈~是啊 这是读书笔记而已~
推荐图书
- 樂而不雅 Lustfully Yours
-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三辑)
- 泛型程式設計與STL
- 孔雀画稿
- 工笔牡丹设色技法
- 工笔老虎画法
- 学画宋画花鸟
- 色彩静物
- I中小学安全教育实验读本3年级上
- I中小学安全教育实验读本1年级上
- F中小学生甲型H1N1流感预防教育手册
- 放大本王羲之传本墨迹
- 放大本颜真卿祭侄稿
- 工笔传统山水画法
- F小学新路径英语彩色8
- 儿童创意学画
- 儿童创意学画
- 儿童创意学画-物品交通
- 儿童创意学画
- 放大本米芾蜀素帖
- 放大本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修小园子帖
- 放大本张芝冠军等五帖
- 放大本钟繇荐季直表宣示表
- 新课标2013全品中考复习方案 语文 听课手册+作业手
- 新课标2013 全品中考复习方案 数学 RJ 听课手册+作业手册
相关图书
- 脱下开裆裤的香港
- 女優・アイドル400名衝撃場面!
-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研究
- 国际气候变化条约的遵守机制研究
- 映画の授業
- 柏林黄昏
- 上古史故事新编
- ヒットの理由
- 悪趣味邦画劇場
- 中国农民画
- Mastercam软件应用技术基础
- 海淀名校.第课一考.五年级数学.下 北师大版
- 前進北京藝術區
- 2010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 大纲变化 基础练习 真题提
- 美国风情录(英汉对照)
- 湖南省机动车驾驶人科目考试标准题库
- A Girls 似曾相識01
- 香港:重複的城市
- A Girls 似曾相識02
- A Girls 似曾相識03
- 「人を殺してはいけない」と子どもに教えるには
- C++ 编程规范
- 範馬刃牙20
- 漂ノ男子漢外傳:林田傳說(02)
- 魔法老師28